专访美国汉学家罗斌(下):研究文献如何做到“语境化”
2018-07-26 14:28:04凤凰网国学 来自北京市

罗斌(Robin McNeal)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
【导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康奈尔大学罗斌(Robin McNeal)教授开始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并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早期信仰、民俗及文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古文献学的国际知名汉学家。
2018年6月2日下午,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特邀罗斌教授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方法的体会——叙事化的重要作用”。他以“事实”与“话语”的新颖形式深入浅出地表达了探寻“话语背景”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挖掘“事实”与“话语”的深层内涵,6月8日上午,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了罗斌教授。
在采访中,罗斌教授表示: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和中国人热情的态度让他长久地保持着对古代中国研究的兴趣。他用“书架理论”生动地描述了中西在神话问题上的互动,同时强调中西方学者在深化研究中应注重考察其历史背景,而非强调其真实与否。在古文献数字人文化可行性上,罗斌教授以《吕氏春秋》和《逸周书》为例,认为大数据在完整程度较低的文献中的应用与传统研究结果差别不大,而在完整程度较高的文献中更具应用前景。访谈还针对“事实”与“话语”进行了提问,罗斌教授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可能无法确定某一记载是否属实,但可以研究记载背后的历史语境和历史影响,寻找“历史真相”。
罗斌教授在访谈中表达了他关于历史观的两层含义:一是“话语”中的“历史”层面,研究者应探寻“话语背景”,还原“历史真相”;二是真实历史层面,研究者应考证“话语”内容,回归历史真相。罗斌教授认为这两个过程中文献使用牵涉甚广,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有耐心、坐得住冷板凳。
以下为整理后的访谈实录(下):
处理文本中的“事实”与“话语” 应持怀疑与批判之态度
凤凰网国学:您之前讲到“事实”与“叙事”,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史学家在研究中,将这二者处理得比较好的例子吗?
罗斌:虽然很多历史学家一直在用这个方法,但严格来说,我是第一个去讲具体用这个方法的人。我刚刚提到的顾颉刚,他一直在用这个方法,但近二十多年来有人批评顾颉刚,其中有一种批评是:认为他过于怀疑会犯错误。用这种方法会犯错是难免的,但若因为几个小错误就拒绝这个方法是不对的,他采用“疑古”的方法,用所有的文献和资料去怀疑,探索这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献,做出研究成果后,给下一代人参考研究,但这样的过程不一定完美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举个例子,春秋时期吴国的祖先是文王祖父的儿子,他叫太伯(又称泰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太伯应当是下一任周王,但他见自己的父亲很中意他弟弟的儿子姬昌,也就是未来的文王,在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太伯和弟弟仲雍离开了周朝,逃到了南蛮之地吴国,这相当于从文明的中心跑到了边缘。太伯与仲雍“断发文身”,接受当地习俗,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于是上千小部族自愿归顺太伯,吴地的人被这位大圣人教化了,变得有文明,他就成为了吴国的祖先。
换句话说,这个故事从另一角度讲,吴国想进入中原文化系统,中原国家会认为吴国是南蛮之国,不想跟吴国进行交往,但吴国就认为我们的祖先比中原国家的祖先更有权力,能够真正称得上王,为了能够进入中原文化,就会去寻找能与中原相联系的脉络渊源,故事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不确定这个故事有多大可能性是真的,但我认为99.9%的可能性是假的。再说越国的祖先是谁?是大禹,越人会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比吴国、周朝还要厉害。这个故事也是从话语去理解,不要把它当成事实,而且最早只能出现在春秋晚期的文献中,西周时,他们不讲太伯让位,因为这个故事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这个肯定是后来才讲的。

《论衡》里说得很清楚,它说太伯为什么选择到吴国(在周朝还没有授封时当然不叫吴国),当时吴国还是比较野蛮的,他们会剪头发、刮胡子、纹身,太伯到了吴国也做了这些,当他被请回去当王时,不能祭祀祖先,因为纹身、剪头发是对祖先的不敬,不能进入祭祀的地方。这一听就非常有故事色彩,我百分之百认为它没有任何事实性,我没有办法证明,也不需要证明和否认,因为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应该研究或者探索的是为什么当时的吴国人会这么说,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虽然吴、越两国在当地是很强大的国家,下面有很多附属国家,但它自己成不了一个大系统,他们需要与中原往来,不仅在经济上有往来,在文化上也希望有往来,以故事串故事将吴、越与中原文化联系,拉近与中原的距离。
凤凰网国学:您在讲座中也提到了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即不应该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以您的经验来讲,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处理文本中的“事实”与“话语”?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界定的标准,应该如何界定?
罗斌:我一直在讲,要用怀疑、批判的态度,但这个可能过了。比如说这个桌子是真的、假的,都没法证明,这就比较过分。现在西方人文科学里面,就存在这个问题,什么都是假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你可以怀疑它,虽然没法全部弄明白,但是你能够提供一点点东西,在前人基础上有一点进步就够了。比如那些想当医生的学生,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幻想,以后要治疗癌症,但最后都失败了,就产生不当医生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辈子能够救助几个人、帮助几个人就已经很好了。研究历史,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态度,虽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理解太伯和吴国的关系,但是我们起码能够把我所做的研究贡献出来,供后人参考,研究历史就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如何研究文本“语境化” 需了解更多更复杂的材料
凤凰网国学:在您对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五儒家经典》(The Five Confucian Classics)的书评和Danner对您《征服与统治: <逸周书>中的中国早期军事文献》(Conquer and Govern:Early Chinese Military Texts from the Yi Zhou Shu)的书评中都提到了“contextualize(语境化)”,“语境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当我们认识到“语境化”的重要性后,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语境化”呢?
罗斌:这个可以回到哲学与历史差别的问题上。比如,我看《道德经》,关心的是《道德经》中有什么值得学习,或者提出了某个真理的东西。但哲学家不一样,他完全可以脱离《道德经》的历史背景、思想背景、政治背景,只追求精神的超越。历史学家就不一样,他们认为可以超越时代所产生的东西还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像我就想要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语境化”的意思是说看《逸周书》或者其中的某篇,或者是吴国祖先的故事,我们更希望把这些文献放到当时的思想、历史、政治背景下,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版本以及对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样才有可能理解《逸周书》或者吴国祖先的故事。所以,这个是“事实”和“话语”的问题,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出现在吴国历史上,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了解故事背后的目的,可能与吴国想进入中原文化,将家谱与中原相连接有关。虽然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能清楚历史背景,但是你“语境化”后,很容易注意到一些重要的问题,而忽略一些没法回答或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但是“语境化”还是必须弄清楚它的年代,它往往是围绕着它的“语境”。
当我们认识到“语境化”的重要性之后,如何做到“语境化”呢?我有个建议,比如你研究孟子、荀子,你越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可能走的越是哲学的方法,就会局限在孟子、荀子抽象的理论上。你不要仅仅只是研究孟子、荀子的文本,要把同样的问题放到整个战国的背景,尤其是和它有些距离的如《吕氏春秋》等文献中寻找,你就会慢慢地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比如,当时的人们对“人性”好坏的看法,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认为他们讨论的是另一个题目,他们讨论自然的和人为的东西,儒家所讲的那套是自然有的还是人为创造的?荀子认为是人为创造的,但他又说不清楚,他的意思是文化不是自然的,是圣人创造出来的,因为圣人有通天的本领。孟子就不模糊,他认为儒家的孝、义不是人为创造的,而是天生就有的。庄子跟孟子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庄子的基本看法是儒家的那套东西是假的、不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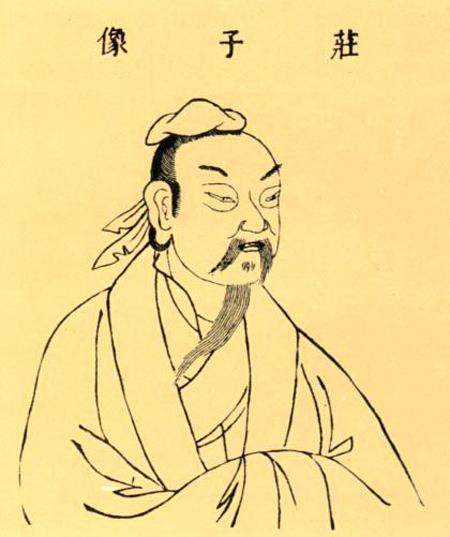
我想举《大宗师》中的“相濡以沫”的故事,庄子的意思是把池子里的水抽干后,很多鱼在那翻来翻去,彼此吐泡沫维持呼吸,原来是要干死了,后来因为彼此吐泡沫,还能多活一个小时,这个泡沫就好比儒家提倡的礼、义、孝等。你说它有用吗?在它快要死亡时彼此吐泡沫是有用的,但是我追求的是回到有水的状态,我游我的,你游你的,不需要彼此吐泡沫,所以庄子讲自然。孟子就认为这个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天生就有的,他讲萌芽时用的比喻也是自然界中的比喻,这个东西是自然产生的,只不过需要我们培养。荀子又更矛盾,他想说其实是人造出来的,但是他又很难回答为什么这套比创造出来的另外的要好?最后,他只能说是圣人创造的。他的心理是非常矛盾、复杂的,他崇拜尧舜禹,认为我们都可以当尧舜禹,但事实上只有那几个人是尧舜禹。这是一个“语境拼接”(contextual composition)的问题,多看资料,不要纯粹只看哲学作品,需要看更多、更复杂的资料。
*以上经罗斌(Robin McNeal)教授审订并授权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