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陈方正:人类进化到突变点 东西方人文精神如何面对
2019-10-31 12:52:59凤凰网国学 来自北京市
【导言】“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山崩海啸,天地变色的大时代。我们有足够勇气正视和迎接未来吗,还是会任由让未来淹没自己呢?萨特说得好,这是每个人都要回答,都要向自己负责的。”最近,《中国文化》杂志刊登一篇重磅文章——《论人文精神与未来世界》,作者是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陈方正先生。他在此文中指出:人类四百万年来的整个进化历程,都是由(广义的)科技变革所推动,而此历程目前已经达到一个突变点,今后人与人类社会整体的变化,将颠覆过去五千年人类文明所累积的人文观念,面对此不可测之巨变,人类必须对本身今后之命运加以深思并作出抉择。
以下是《论人文精神与未来世界》的全文,凤凰网国学频道受权转载。

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
现代科技进步迅速,从而令环境不断变异,熟悉的事物不断消失,以致人有如永远置身异乡,心境无时宁适。因此寻找人的本性、本质,重新发扬“人文精神”的呼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但到底何谓“人文精神”?它为何会失落?当如何重建,又是否有可能重新发扬?那却是人人言殊,难有定论。本文所要尝试的,是撇开重建“人文精神”的崇高目标,而将之视为历史上曾经重复出现的文化现象,以将它的意义和处境看得更为清楚。这样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宋代新儒学是一个对应佛教挑战,恢复与发扬以人为本理念的运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中“文”的部分正是“人文主义” (humanism) ;法国哲学家萨特断言“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而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则著有《人文精神之重建》,等等。但这几个运动分别属于东西两大文明,时间前后相隔千年,彼此似乎绝不相干。那么,它们到底有无共通之处呢?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相类似的运动吗?它们与现代世界的变迁又有何关系?
这些问题的探索将引领我们面对另一个大问题,即人在未来世界将面临何种变化。在过去,这问题并不存在。在“天”抑或“神”主宰世界的时代,“人”的本质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譬如,是具有天生仁心,或者不灭灵魂。但在科技飞跃发展的今日,这观念已经崩溃。问题不再是人的本质如何,而是人类在未来世界中将会变得如何,亦即将处于何等地位,具有何种意志、心态了。不少人可能仍然认为,未来世界既然是由人所建构,那么它也必然是根据人的意志设计,因此不可能违背人的“需要”或者“本性”。但如下面所将论及,这传统观念其实是对人,对世界的重大误解。无论如何,“人文精神”与“人性”不可分割,因此它与人在未来世界的命运亦息息相关,讨论人文精神的前景必然要牵涉到未来世界,原因即在于此。
本文共分四节,前两节回顾和分析在东西方颇有代表性的五个人文主义运动,即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宋代新儒家、欧陆存在主义、美国的社会批判思潮,以及中国当代新儒家。后两节则分别讨论人文领域与科技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文明演化的展望,从而为人文主义在未来世界的前景勾勒一个轮廓。这个讨论无可避免要牵涉许多似乎渺不相干的领域,因而将显得十分庞杂和头绪纷繁。至于它是否有意义,则只有留待读者教正了。
一 文艺复兴与宋代新儒学
在现代以前,人文精神重建的两个最佳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中国宋代新儒学,它们的具体发展过程与所带来的后果大不一样,但背后的精神却十分相似。我们在下面先简单描述其梗概,然后再作比较。
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北部[1],包括“文”、“艺”两个不同部分[2],前者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3]。在其初,人文主义仅指学习拉丁文法,发扬拉丁文学,有点像唐代的古文运动,随后则扩大到搜集、考证希腊罗马古代典籍,以至研究古代思想,追求古典文明的“复兴”(renaissance)。这个运动的大背景是:欧洲的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在4-10世纪这七百年间遭受两个沉重打击:先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有意识地压制异端学术;继则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文化火炬熄灭。
对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是起源于巴勒斯坦的外来宗教,它取代原有学术文化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吸收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精华;其次,通过论争贬抑俗世文学和学术[4];最后,推广修道院文化,把俗世学术从当时有识之士即教士的心中驱除净尽[5]。这整个过程经历了六个世纪(约400-1000 CE)方才大功告成。然而,到了12世纪,由于三方面的契机,希罗古典文明却又复苏之势。首先,在10-13世纪间,由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斗争,意大利北部城市乘势崛起,互相兼并,最后只剩下十几个独立成邦。它们不再依靠农业,而致力于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发展成富裕和多元社会,不再受教会、君主或贵族控制[6]。其次,古代希腊罗马典籍在黑暗时期失传,但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而得以保存在伊斯兰文明中。从12世纪开始,许多欧洲学者将它们翻译成拉丁文,使欧洲得以重新接触古代文明。最后,古罗马法律体系没有完全断绝,而是通过意大利北部的公证人(notary)制度延续下来。在公证人的教育中,拉丁文极受重视,那就是人文主义出现的温床[7]。
人文主义在13世纪萌芽,那时北意大利已经出现仿效古代文学体裁的拉丁文作品,它们受古罗马作家影响,主导观念从基督教转向个人意识和追求[8]。人文主义第一位大师佩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就是受其影响而崛起[9]。他出身佛罗伦萨公证人世家,虽然当了教士,却不屑处理教会事务,更不愿进修道院,一生追求柏拉图式爱情,以写作为终身志业。他崇拜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Cicero),文体仿效古代的传记、史诗、爱情诗歌、凯旋颂歌、颂扬辞章、忏悔录等,由是得成大名,皇侯争相罗致,并受加冕为桂冠诗人。这样,通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近千年,拉丁文学终得重放异彩。
佩特拉克对同时代学者影响极大,最重要的是佛罗伦萨的沙鲁达提(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他是著名文人和政治家,有能力和地位搜购古代书籍、文献,1397年从君士但丁堡请来名宿克拉苏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教授希腊文,奖励后进,掀起人文主义风气,培育了再下一代学者。其中罗西(Roberto de' Rossi,1355-1417)是希腊原典翻译家;尼可洛(Niccolò de' Niccoli,1364-1437)是藏书家;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 -1444)是沙鲁达提的学生和政治继承者,翻译了大量古籍,撰写了佛罗伦萨史以及西塞罗、但丁、佩特拉克等人的传记,又鼓吹佛罗伦萨公民意识和共和体制,影响日后民主政治的发展;波吉奥(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则孜孜不倦搜求和发现了大量古代手卷,包括失传已久的卢克莱修(Lucretius)长诗《自然之本质》[10]。
到十五世纪下半,人文主义开始散播到佛罗伦萨以外,这时期最重要的两位学者是那不勒斯的瓦拉和荷兰的伊拉斯谟[11]。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推崇伊壁鸠鲁哲学,专研究拉丁文体和修辞,以证明教廷视为至宝的《君士但丁封赠书》为伪造成大名。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5-1536)凭自学成材,他多次访问英国,和《理想国》(Utopia)的作者摩尔(Thomas More,1478-1535)惺惺相惜,最后定居巴塞尔。本来人文学者绝少讨论基督教,他却起而反对经院哲学,提倡人性与宽容,又出版经过详细考证的《新约圣经》希腊文—拉丁文对照本,这在宗教改革中成为新教的重要依据[12]。到16世纪,人文主义传统还有一位殿军,即法国散文家蒙田(Michel Montaigne,1533-1592),他厌倦宗教冲突,思想倾向于怀疑论,被奉为现代哲学前驱[13]。
人文主义兴起是欧洲思想史上戏剧性的巨大转变。它毫无挑战基督教的意图,实际上却使得古代文明在罗马教会赞助甚至鼓励下复活。也就是说,人文主义者操戈入室,以最微妙,最平和与不经意的方式颠覆基督教理念,无形中瓦解了教会占据欧洲心灵殿堂的千年之功[14]。这可以说是人文精神重建的最成功例子,它显示欧洲古典文明是如何丰富、强大和坚韧,虽然经过千年沉睡,仍然能够破土而出,焕发新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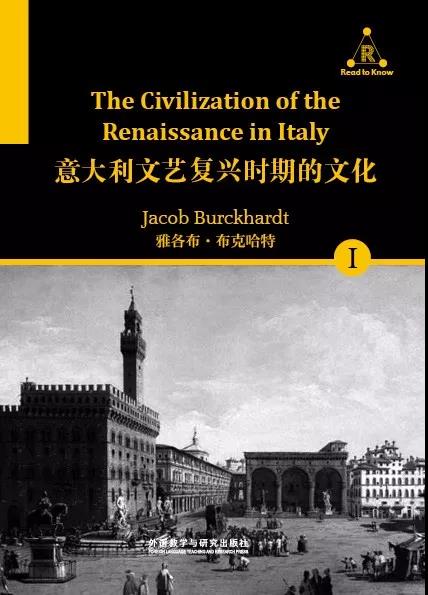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宋代新儒家
宋代新儒学出现的背景和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表面上有些相似,但底子里则大不相同。相似之处是,自东汉末年以来佛、道两教在中国蓬勃发展,到宋代已经有七百年历史,它们在思想、社会和政治等三方面都对儒家构成极大挑战。首先,佛、道各有一套形而上结构和玄妙理念,那是原始儒学所缺乏的,因为它向来不谈“性与天道”,而专注于人间秩序,故此“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其次,儒学以君子即社会精英为教诲对象,因此无法在民间与普世性信仰如佛道抗衡。最后,自隋唐开始,历代君主一面倒崇奉佛道,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却因谏迎佛骨而“夕贬潮州路八千”,那正好说明当时儒学地位之严峻。
两个运动不同之处在于,新儒学的兴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15]。宋代自开国便处于军事弱势,而为了改变前代兵骄将悍的格局,君主又要崇文抑武。士大夫由是生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与承担,以及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期待与自信。而这自信则是通过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建立起来的[16]。除此之外,它的思想渊源也相当复杂,不但将儒家经典的范围扩充到《大学》、《中庸》和《易经》,而且与佛、道二教也有千丝万缕关系。
整体而言,宋代新儒学的出现大致有三条脉络。首先,它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陈抟老祖(约871-989)[17],那是一位时代跨越唐宋,通过《易经》象数和《老子》来讨论宇宙生化原理的道士,他的河图洛书之说影响了邵雍(1011-1077)和周敦颐(1017-1073)。陈抟是山林隐逸;邵雍与司马光交厚,大隐于市;周敦颐则一度出仕,他就是将易、道思想与儒学结合的关键人物,与王安石有交谊,亦曾开导二程。其次,新儒学的中心思想是“内圣外王”,即深湛、完善的内心修养是舒展政治抱负,安排合理人间秩序的必要条件,而后者又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这个观念发微于韩愈,在王安石变法时颁行的《三经新义》中提出来,最终为二程和朱熹所接受。换而言之,新儒家是通过“道体”、“道统”和“治统”的论述,将他们修养心性那一套自省功夫作为政治改革基础的[18]。
最后,新儒学和佛教也有千丝万缕关系。韩愈排佛,宋初的柳开(948-1001)、欧阳修(1007-1072)承接其古文运动反对佛教;宋初三先生孙复(992-1057)、胡瑗(993-1059)和石介(1005-1045)虽然曾在寺庙借读,也同样从传统儒学角度辟佛。然而,此时的高僧如智圆(976-1002)和契嵩(1007-1072)禅师高瞻远瞩:他们精研韩文,一方面对韩愈和柳开等的辟佛作出反击,另一方面则承认儒学在治国方面的功能,并经常与士大夫交接谈论,由是左右舆论。其影响所及,《中庸》从《礼记》被抽出来成为朝廷特别重视的独立篇章,也很可能是出于有佛教背景的士大夫之推动[19]。因此新儒学与佛教虽然对立,亦不乏深层内在联系。
综括而言,新儒学是通过吸收《易经》和佛、道思想,来深化和扩充原始儒学内涵。它在北宋兴起,至南宋发扬光大,到明代更由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而从士大夫扩散到民间下层。然而,它缺乏超越此生的论述与应许,所以无从蜕变为大众化宗教,扭转佛、道盛行不衰的大趋势。至于在政治上,它亦只成败参半。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无疑再度确立了儒学在国家体制中的独尊地位。但司马光的新政和安石的变法同以失败告终,明朝更转向君主独裁,由是书院被禁毁,以廷杖凌辱大臣屡见不鲜,“得君行道”和“共治天下”的理想完全幻灭。王阳明之从“内圣外王”转向以内省为中心的“致良知”说,缘故实在于此[20]。
两个人文主义运动的比较
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和宋代新儒家有惊人相似之处。它们都代表以“人”为中心的古代文明精神(这在中国是儒家,在西方是希腊和罗马文化)被外来宗教(在中国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21],在西方是从巴勒斯坦传来的基督教)渗透、掩盖甚至征服之后,由于具有古代文化意识和自觉的学者之努力,古代文明得以重新振兴,并且发展出更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所以两个运动都不折不扣是“人文主义之重建”,也就是在已经被宗教主宰的世界中,重新彰显人本价值和精神。这显示,全面感染中国和西方的高等宗教虽然声势浩大,但具有深厚底蕴的古代文明仍然蛰伏于集体意识之中,时机成熟就能够破土而出,焕发新生命。它们另一个相似之处是,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学者几乎全部任职于罗马教会或受其供养,而推动新儒学的士大夫则多与禅师、佛徒、道士密切交往,思想亦交互渗透影响。这反映新旧两种文化力量虽然在理念上并不一致,但代表这两种力量的人却不一定互相排斥,积不兼容,而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密切交往。
但从后果看来,则这两个运动的影响力却相去甚远,不啻霄壤。在社会上,新儒家未对佛道二教产生强大冲击,更谈不上颠覆它。在思想上,它从这两个宗教(当然还有传统经典如《易经》和《中庸》)吸取了宇宙生化观念和修养功夫,以充实和发展自身。在国家体制中,它重新巩固了本身的正统地位,但亦未能打破儒、释、道三者原有的势力平衡。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特别是人文主义则无异于掀开了潘多拉盒子,古代希罗文明尚未发挥的潜力由是得以充分释放。其最重要的三个后果是:首先,16世纪发生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罗马教会定于一尊的格局由是崩溃;其次,它间接促成了17世纪科学革命,由是完全改变人对大自然的观念。最后,以上两者转而导致18世纪启蒙运动,那带来了理性主义、世俗化思潮以及法国大革命,现代世界就是从这些翻天覆地的巨变中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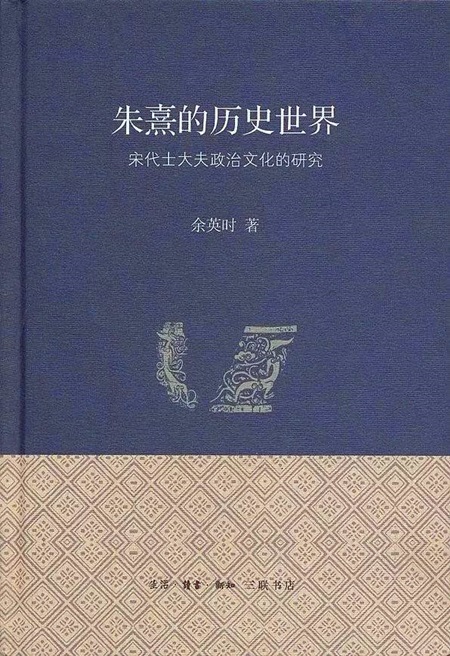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二 存在主义、社会批判思潮与当代新儒家
启蒙运动不但强烈冲击基督教,而且改变世界,导致了以科学、理性、宗教之“解魅”(disenchantment)为特征的现代世界之出现。无可避免地,现代世界又产生了对它本身理念的各种反应,那大致上可以归为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国的社会批判思潮,以及中国的当代新儒家运动等三类,每一类之中又可能包含若干不同思想。
欧洲存在主义
文艺复兴触发了欧洲思想的滔天洪水,此后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接踵而至,一发不可收拾,彻底摧毁了基督教的主宰地位,改变了欧洲的精神面貌。自此上帝被“解魅”(disenchanted),“理性”取代“信仰”,重新占据西方心灵的中心。如此天崩地裂,沧海桑田巨变自然要引起各个领域的强烈反应,其最早、最直接的就是开始于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运动。它反对理性桎梏,强调个人感情的抒发,向往于孤独与大自然,影响非常广泛,诸如歌德,拜伦、济慈、华兹华斯、布里克、柯罗列兹等的小说、诗歌,贝多芬、舒曼、李斯特、肖邦士等的音乐,法国德拉克罗的绘画等等都是其代表。
对上述巨变特别是其俗世化思潮的反应则来自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22]。它出现稍晚于浪漫主义,影响之广泛和声势之浩大也有所不及,但深入和持久则过之。这一运动可以丹麦的祁克果、德国的尼采、法国的萨特等三人为代表,他们时代不同,倾向各异,其间的分别正好反映了这个运动在19-20世纪百余年间的演变[23]。
存在主义的先驱是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24]。他自幼孤癖、瘦弱、为严父权威阴影所笼罩,而立之年出版《非此即彼》(Either/Or)和《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其后创造力持续近十年。他的思想以上帝和个人为中心,联系两者的,是人对上帝的彻底、绝对、无保留服从——正如《创世纪》中阿伯拉罕服从耶和华的命令,准备把老年所得爱子杀死献祭一样。他鄙视丹麦讲究理性的新教教会,认为基督教教义里面那些荒诞、不合逻辑、不可解之处正为其可信之处,企图用理性来解释它们是可笑、无用的。换而言之,他是以复古来对抗理性精神,认为真理必须主观信服,而不是拿来讨论的。在强大的世俗化思潮面前,这无异于吉诃徳攻击风车,而比他更愤激的西班牙存在主义哲学家乌纳穆努(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所歌颂的正就是吉诃徳精神[25]。
但愤激无济于事,到了20世纪,存在主义神学家、社会学家诸如田力克(Paul Tillich,1886-1965)、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等就都已经和现代世界妥协,他们只不过是要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来为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寻求意义和立足点,而再没有以基督福音重新征服世界的气概了。不过,对大众而言,这其实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因为在现代,各种基督教派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哲学家、神学家所看到的严重教义问题,一般人根本不关心:他们需要的,是福音、慰藉、团契、永生盼望,而并不是自洽的真理。
晚一代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比祁克果名气更大,思想更复杂,著作更丰富,诸如《查拉图斯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善良与邪恶以外》(Beyond Good and Evil)、《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看哪,这个人》(Ecce Homo)等等都脍炙人口。和祁克果相反,他看不起基督教,而尊崇古希腊理念,认为他们提倡的是“主人道德”,以高贵、勇敢、慷慨为尚;罗马帝国下层民众亦即基督徒所宣扬的是“奴隶道德”,所以讲求谦卑、柔弱、节制,压抑天性和欲望。他自己的理想类型则是能力强大,能够自我节制,而不须听从外来道德指令的“人上人”或曰“超人”(übermensch),因此干脆抛弃普世性道德观念,代之以适合不同个人的文化理念。他看到了基督教的没落,故而喊出“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祂的”[26],一语道破天机。
尼采证实和接受基督教的没落,因此回到其前的古希腊理想,重拾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巴门尼底(Parmenides)精神,把只宜于少数智力高超者冷静研究的问题,用谜样、悖论式语言写出来,挑战一般读者头脑。不幸的是,这不但没有能够为知识分子指点出路,反而(应该说是无可避免地)引起巨大误会,从而为纳粹所利用,那是其哲学和他个人的悲剧。
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一生丰富传奇,多姿多彩,既是学院派现象学家,以现象学巨著《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知名,又是小说家、二战时抵抗德军的地下战士,反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反越战的左派政治活动家、社会运动家,更以与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爱情和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知名。对我们而言,他最重要的自然还是1945那篇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为题的演讲[27];他“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以及他的道德观,那就是人生于世,是无依无靠,无可凭借,也绝不可推诿责任的,所以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来选择一生道路,并且为此和所有行动的后果负责——那就是人的基本存在状况,也是他焦虑的根源。
萨特深受沦陷法国的地下抗争世界影响:“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孤独存在,要完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哲学和那个严酷处境不无关系,但不能说是由之决定。无论如何,那正好代表西方人在失去已经延续千五百年的基督教精神家园之后,所面临的孤寂和彷徨。不像齐克果、乌纳穆努或者尼采,他并不在困境中莽撞、呼喊,或者提供貌似可能的出路,而只是冷静和无情地指出和刻画现代人的困境,亦即其“存在状况”。那也就是他为人熟知的小说《无出路》(No Way Out)和贝克(Samuel Beckett)的荒谬剧《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之由来。
他们三人的呼唤各不相同,却都是以人为中心,而且,和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存”恰恰相反,他们所讲所关注,并不是单纯有思想的,一个由哲学或者宗教观念设定的人,而是活生生,有七情六欲,在现实中行动生活,不受任何前设观念拘束的人。在基督教理念破灭,理性与科学观念入主西方文明之后,这是哲学家对它的全面抗议和根本反叛。萨特比祁克果和尼采都更为客观和成熟,他不啻宣称:是的,自然被解读了,它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都被科学家发现了,但人和其它自然现象不一样,因为他没有本质,他的存在高于一切,因此是完全自由,不可能被解读、发现、限定的。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很重要,下面还要深入讨论。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译本
美国社会批判思潮
存在主义是由启蒙运动,也就是基督教之被“解魅”所引起的反应,所以表现为哲学运动。但宗教“解魅”只是开端,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还有连串其它后果:民主政治、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现代科技,等等。统而言之,那就是以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tic order)为基础的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之出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正是其典范。这个社会表面上富裕、松散、自由,其实背后有强大组织和严密控制,它们所激起的反抗就是我们所谓社会批判思潮,其中突出人物有三位:马库斯、乔姆斯基和布鲁姆。
马库斯(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萨特一样,也出身德国现象学派。纳粹兴起后他跟随法兰福克学派的“社会研究所”流亡美国,二战期间成为情报专家,最后回归学界,在1964年以《单向人》[28]一书倾倒年青学子,那正当民权运动、反越战、活斯托(Woodstock)音乐节、法国学生和工人掀起革命的火红年代。此书主旨很简单:资本主义与科技结合之后,其力量是如此巨大,物质回报是如此吸引,以致社会体制能够“入侵”和“辗平”个人内心,使得它失去独立向度或者意志,再也无法抗拒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思考其它不同社会体制——例如工时限制,公共医疗体制等等[29]。换言之,在此社会中,人已经从意识上被彻底压扁和“物化”,成为科技所建构的巨大生产机器一部分,再无独立思考的能力了。他是悲观的,承认“社会批判理论”虽然正确,却“缺乏能够跨越当前与未来之间鸿沟的概念,没有成效更无展望,因此只能够消极。”[30]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集激进社会评论家与语言学大宗师于一身[31]。他出生于大萧条和西班牙内战年代,在纽约左翼分子影响下成长,于六十年代受民权运动和越战刺激,成为反建制斗士,以虎虎生气与锐利笔锋全面攻击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包括学术界和传媒。他的政治与文化观点简单直白,即美国是由垄断性企业控制的社会,对外政策纯粹是为了扩张势力,知识分子和传媒表面上监督政府,实际上沆瀣一气,制造多元假象,企商政学传媒各界实际上已经形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唯有唤起民众的普遍觉醒方才有改变此状况的可能。
最后,是耶鲁英文系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 )和他的《西方经典》[32]。那是一部讨论西方文学名著的大书,从但丁、乔叟一直谈到惠特曼和贝克特,它在学界轰动一时,关键在于它第一章“经典的挽歌”,以及最后一章“挽歌作结”的这几句话:“在……性别和性取向理论家,还有数不清的多元文化拥护者环绕之中,我意识到文学研究之四分五裂是无可挽回的了……西方文学的研究也会继续,不过规模将小得多,像现在的古典语文系一样。现在所谓“英文系”将会改称“文化研究系”,那里超人漫画、摩门主题公园、电视、电影和摇滚乐将取代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华斯华兹和史提芬斯…这变化没有什么可惋惜的;现在耶鲁的新生对阅读有真正热情的已经寥寥可数了。”[33]换而言之,西方学术殿堂中的建制派虽然和马库斯和乔姆斯基大异其趣,但对当代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却也同样痛心疾首[34]。
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关心的是基督教没落后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境,至于美国社会评论家所关心的,则是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宰制社会之后,个人在其中的愤懑、困惑与无奈。这种困惑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向度,但归根究底,则都是来自一个高度理性化、工业化,具有高度层级化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的大众社会对于个人的控制、压迫与侵蚀。这社会以提供层出不穷的各种消费品来换取一般民众的支持;以较优越的经济地位和精巧建构的理论来保证精英阶层对资本主义的认同;而将所有阶层都联系起来的,则是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秩序,它保证了社会在多元诉求冲击之下的稳定。马库斯慨叹的,是在此强大意识形态宰制下,个人独立思考能力之迷失;乔姆斯基所希望打破的,是这社会的精英阶层所协力维护的稳定层级结构;而布鲁姆所感到无奈的,是消费主义所必然带来的低俗文化。整体而言,他们都是在批判、抗议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大众社会的某些面相。但他们所正面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却不很清楚,也许只可以笼统地描述为,个人相对自由、独立、松散,思想上能够享受更大自主空间的那种状况——也就是在结构上接近于前现代社会的状况。至于这是否能够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要求兼容,则罕见讨论。
当代新儒家
中国受到西方冲击开始于鸦片战争,重大危机感出现于八国联军之后,其后反应在政治上导致了辛亥革命,在文化上则分为两途:主张接受西方理念的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主张伸张传统文化的则流派繁多,当代新儒家是其中具有明晰哲学观点的一支[35]。
新儒家第一代以号称“三圣”的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为代表,他们在文革前活跃于中国大陆;第二代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三位熊门弟子为代表,他们从五十年代开始活跃于香港和台湾。第一代新儒家深受佛学影响,这和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在世纪之交从儒学转向诸子学和佛学以寻求与西方抗衡的思想资源颇为相似[36],但渊源可追溯到杨文会(1837-1911):他在1866-1874年间筹办“金陵刻经处”,1879年跟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彼与日本东本愿寺的南条文雄交往,得到他协助搜求散落在日本的佛经,1907年成立“只洹精舍”;他的弟子欧阳竟无(1871-1943)在1922年创办“南京支那内学院”,那成为振兴中国佛教的中心之一[37]。
马一浮(1893-1967)祖籍绍兴,曾习数种外文,并逗留美国一年,对西学一度深感兴趣,但在辛亥革命前后受了刺激而隐居西湖三十多年(1905-1938),为学转向老庄和佛学,最后回到儒学,以“六艺”为依归[38]。他往来的人除梁漱溟、熊十力以外,主要以佛门为主。七七抗战是一转机,他受激发为浙江大学作“国学讲座”,又在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39]。熊十力(1885-1968)出身湖北黄冈农家,不到二十参加武汉新军,辛亥革命之后发愤读书,也曾为护法运动奔走[40]。他在壮年出版崇佛抑儒的《心书》(1918),因此结识梁漱溟,经他介绍到南京跟随欧阳竟无(1920-1922)研究唯识学,从而得以进入北大等高校讲学。他起初深入研究佛学(1920-1925),写成《唯识学概论》[41];旋由佛归儒,否定轮回说,对人生采取积态度,出版《新唯识论》(1932),和佛门中人论战[42]。他在晚年(1956-1961)有《原儒》、《体用论》、《乾坤衍》等多部著作,从而完成了以《易经》为儒学中心的思想体系。解放后马、熊二位颇受照顾和尊重,却未能逃过文革劫难。

马一浮全集
梁漱溟(1893-1988)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得得父亲的开明教育,不到二十岁参加同盟会,辛亥之后理想破裂而转向佛学,作《究元决疑论》获蔡元培赏识,得以任教北大(1917-1924)。其间他赴南京向欧阳竟无求教唯识学,旋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比较中国、印度、西方等三个文明,宣称中国文化行将复兴,因而成名[43]。此后他辞职开展乡村建设理论和运动,抗战期间积极参政,但都没有成果;1947-1950年间在北碚勉仁国专讲学,1941-1949年间写成《中国文化要义》。解放后他受特殊照顾,虽然性格耿直,却仍然能够渡过文革劫难,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新儒家的第二代唐君毅(1909-1978)和牟宗三(1909-1995)经历相似,都就读北大,有机会亲炙熊十力和梁漱溟,成为熊的弟子,同时接触到西方哲学。抗战时他们各自发展哲学思想,1949年后活跃于港台两地,最后都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彼此交谊深厚,相互欣赏[44]。但他们路数不同:牟致力于形而上建构,通过所谓“良知的坎陷”来跨越中西文明的鸿沟,唐则试图通过宗教、道德、科学、艺术等文化意识的阐述来消融中西隔阂,《人文精神之重建》(1954)即为其成果[45]。至于徐复观(1903-1982),也是生于湖北黄冈,出身没落耕读之家,曾就读湖北第一师范、省立国学馆,和留学日本(1928-1931),其后投身军旅(1931-1946),曾赴延安接触中共领导人,其后一度成为蒋介石幕僚,又曾到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46]。他流亡台湾后到东海大学教书(1955-1969),自此投身学术工作,致力于两汉思想史的整理,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与现代自由民主理念关系的反思。1958年他联同唐、牟、张君劢等四人共同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1年为文痛斥胡适诋毁中国文化,再次掀起激烈的中西文化论战,当代新儒家的理念由是得以广为阐扬[47]。
相对于西方自19世纪以来的各种人文精神重建运动,现代新儒家在理念上的诉求简单直接得多。它是站在中国人立场,对于西方文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冲击作出反应,也就是申明: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仍然有其作用和价值,甚至比西方所赖以建立其庞大优势的科学与技术更为重要。这价值何在呢?说到底,便在于对宇宙运行和发展原理的形而上学之了解,以及“仁心”在其中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现代新儒家坚持“仁心”亦即传统道德理念的无上地位与重要性,但并不否定现代科学与社会建构原则(特别是民主理念)的实际价值。所以他们和对抗启蒙运动“解魅”作用的祁克果或者回到古希腊理念的尼采还不一样,倒是与马塞尔、弗洛姆、田力克等存在主义神学家、社会学家有几分相似[48]。
三 人文领域与科技的互动关系
以上五种人文主义运动时代不同,诉求各异,共同点则在于对当时主流文化意识或者社会状况不完全认同,甚或感到不满,而转向传统理念或者文化,所以整体上表现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至于其为宗教性与否反而无关紧要。佛教和基督教分别在11和14世纪被视为当时人文主义的对立面,但到了19-20世纪则转而被视为人文主义一部分。倘若上述看法不无道理,那么它跟着就会引出三个问题来。首先,人文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有何种内在关系?其次,由于科技飞跃发展,现代世界随之迅速改变,那么在未来人文主义将会变成何种形态,还能够发挥何等功能?最后,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个特例,它显然不能够归为“文化保守主义”,那么它又应当如何理解呢?以下我们就循这三个方向来展开讨论。
人文主义与文化保守的关系
为何人文主义表现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答案在前现代(17世纪之前)与现代其实大不一样。就宋代新儒家和文艺复兴而言,它们的“保守”和历史发展过程有关。东西方的古典文明基本上都以“人”为中心,它们其后都遭遇了以“神”或者其它理念如“涅槃”为中心的外来高等宗教(这在中国是佛教,在西方是基督教)的挑战,而至终为其掩盖甚至征服。这样,原来的古典文明由于种种机缘再度勃兴之际,就很自然地表现为“复古”亦即“保守”的人文主义了。因此其“保守性”是来自古典文明的出现早于外来的高等宗教这一事实[49]。当然,这是仅就其开端而言,它们后来的发展绝不保守,而且富有活力和创造性,文艺复兴更开辟了崭新的现代世界。这在上文已经详细讨论过了。
至于近现代的人文主义之表现为文化上的保守则有不同根源:它们是由于现代科学之出现及其飞跃发展迅速改变世界所造成。我们在上文有关存在主义、美国现代社会批判,以及现代新儒家的讨论中已经很清楚地指出,所有这些不同方向、不同性质的人文主义,都可以说是由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特别是其“解魅”作用而引起的反应——尼采“上帝死了!”的惊呼最能够说明这种强烈感触,而这两者背后的基本推动力量,自然就是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因此,在底子里,近代人文精神之“保守”是源于新兴科学与人文领域间的鸿沟。这早就已经为人注意到了,最著名的无疑就是斯诺(C.P.Snow)所提出的“两个文化”之说[50],但他只是将此作为特殊社会现象来讨论,却没有追究其背后成因。
科技与人文领域间的鸿沟
那么,人文与科学领域之间究竟有何基本分别以至形成鸿沟呢?从它们的外延范围来看,问题并不复杂:人文领域几乎包括了人类传统文化的全部——只有作为现代科学前身的自然哲学是显著例外[51]。现代科学本来起源于传统学术中的这个特殊分支,它在17世纪发生革命性突变,此后蓬勃发展,最后形成今日的庞大体系。至于没有发生突变的传统学术和文化,则大部分被归入人文领域,甚至本来与古代人文精神对立的宗教也不例外[52]。
其次,从它们的内涵看,这个区分也同样可以成立。传统文化的关注几乎全部都以“人”为中心,为根本。儒家讲“仁者人也”,亚里士多德以“目的论”(teleology)来建立他的宇宙观,基督教以人的堕落、拯救和追求永生为核心教义,佛家追求涅槃以超脱此生乃至来生的限制,底子里都是从人本位出发,都离不开“人”的最高渴望和追求。所以就内涵而言,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有不可分割的相同根源。
最后,从“人文精神”的对立面即“科学精神”来看更是如此。科学的大部分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都要以数学亦即量化关系为基础,而不能够单纯用自然言语表达,因此它和传统思维方式有根本差别。人文学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隔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而生。更重要,也更根本的是:现代科学力求“客观”,即完全消除以人为中心的偏见、目的、意向(此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不容于现代科学),乃至从习惯生出的固有观念[53]:它是以大自然而非人为中心的。因此,现代科学虽然是从西方传统之中生长出来,但它已经脱胎换骨,和原来的人文精神迥然不同,两者间鸿沟不仅是社会现象,更是其不同本质的深层反映。
所以,从以上三方面看来,人文领域的确与现代科学有巨大分别,后者的飞跃发展完全改变世界,使得前者大受冲击,人文精神自然要伸张前者,它显得保守是必然的。
传统宗教在现代
人文与科学领域的基本分野既已厘清,就可以讨论以上第二个问题了,即今日世界既然是由科技主导因而不断变化,那么在过去五千年间逐步累积起来的传统文化,以及由之而产生的人文精神,今后还将占据何等位置,发挥何种作用呢?在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现代化浪潮中,受冲击最猛烈的无疑是传统宗教,它们地位之转变最富戏剧性,因此今日的处境也最堪注意,而西欧、中国、土耳其是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法国大革命是政治巨变,也是推翻天主教会法定权利,没收其庞大财产,和取缔众多修道院的宗教和社会革命。这些激烈措施后来部分被逆转,但数度反复斗争之后,天主教至终丧失了它在国家体制中的权力与独特地位,然而其民间的影响力则历久不衰。它不但仍然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来源,滋润大众心灵的信仰,而且其众多宏伟教堂和艺术品也被视为国宝而得以妥善保存。基督教在其它西方国家的命运各异,但至终境况则大致相同,即教会大都经历了“退出建制”(de-establishment)的过程,蜕变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间组织[54]。
在中国,儒家是无形的宗教,它的巨大力量在于其经典被钦定为科举准则,亦即入仕门径;因此之故,它的理念和教训就能够通过各级学校和民间教育,广泛渗透整个政治体和社会。从此角度看来,清朝在1905年颁令废除科举和开办新式学校,也等同于使得儒家“退出建制”,其重要性与六年后的辛亥革命差可比拟。至于随后的五四运动则更进一步,公开举起反对儒家伦理的大纛,那就无异于中国的启蒙运动了。但和基督教在西方一样,儒家学说并没有就此被打倒。不但当时就出现了现代新儒家、学衡派,以及钱穆等维护传统的学者,而且在过去一个世纪间,继起的各种传统主义者不绝如缕,到了最近二三十年,从国家以至民间,弘扬儒学、提倡读经、恢复古礼的呼声、运动和组织更日益增加。所以,中国儒学和西方基督教的现代命运并无二致,即丧失权力和国家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之后,仍然在文明内部发挥巨大影响力。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或可为其写照。
至于伊斯兰教和奥图曼——土耳其的关系却复杂得多。在20世纪初,奥图曼帝国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看到宗教和现代化的巨大冲突,结果发展出两种不同思路。革命党思想家居卡尔(Ziya GÖlkalp)认为,帝国现代化之后,在体制上需要接受西方所建立,以科学与代议政制为标志的普世性现代文明,伊斯兰教则行将从普世文明降格为土耳其独有的传统文化而被保存下来,但他这个长远的构想没有得到实施机会。土耳其的“国父”凯末耳(Ataturk Kemal)战胜希腊入侵军队,挽救国家于灭亡之后大权在握:他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是不作讨论,径直以政治力量强行取消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一切政治、社会、文化体制,以求将国家彻底世俗化。这“壮士断臂”策略在当时的确十分成功,但只是依靠军队作为激进世俗化意识形态的保证,而没有广泛民众基础。所以它虽然维持七八十年之久,但以伊斯兰教为号召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终于在本世纪崛起,并数度敉平军队叛乱,寖寖然有废除俗世宪法之势,将来发展如何,尚未可知[55]。这比之大部分其它伊斯兰国家摇摆于原始教义与现代体制之间而莫所适从,处境自然优胜得多,但其面临的两难基本上是相同的。

陈方正《现代世界的建构》
从西方和中国的发展看来,传统宗教让位于以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为标志的现代政治体制,因此丧失其在国家体制内的权力之后,其影响力自不免大幅消减,但在民间却仍然能够维持相当部分的原有功能。东正教之于俄国、神道教之于日本、印度教之于印度,情况也大抵类是。目前仍然拒绝接受俗世化理念和相关政治体制的,就只剩下许多伊斯兰国家了。它们未来的发展无法预测,但随着经济起飞、贸易和旅游增加、科学知识普遍化,以及互联网影响的日益强大,其政治体制之至终俗世化也将不可避免,问题只在于时间而已[56]。换而言之,在现代世界中宗教退出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转变成民族传统一部分,继续通过其民间影响力而提供人生价值与道德规范,那在伊斯兰世界以外已经成为普世性趋势,所以居卡尔还是很有远见的。
人文领域在现代
在传统文化之中,在宗教以外还有广大的人文领域,它们在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也同样受到强烈冲击,但程度和性质不一,变化也各异。这大致上可以分为文艺、学术和哲学等三方面来看。
我们此处所谓文艺,是泛指包括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以创作为手段,以满足人类感情上各种不同需要的所有领域。科技对它们的冲击首先是突破传统媒介和技术限制,由是戏剧演变为电影、电视、虚拟世界;摄影刺激了印象派、抽象派和波艺术的兴起,由是传统美术观念由是被颠覆。其次是改变人的眼光、感情和生活节奏,诗歌和长篇小说由是让位于悬疑、侦探、科幻小说;民歌、爵士乐、摇滚乐、流行歌曲将民族音乐、古典音乐挤出舞台中央。最后则是文艺和音乐作品的商品化、大众化和随之而来的低俗化,它们的独特、庄严与神圣气质由是被侵蚀消融,其移情力量亦随而日趋淡薄。诚然,传统的伟大作品不可能被遗忘,它们仍然在学校课本、博物馆、艺术节、国家剧院中保存下来,继续流淌在文化血脉中。但布鲁姆的愤慨与叹息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无论国家和有关团体如何努力,它们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正在日渐衰减,取而代之的,是更能够虚拟真实和直接刺激官能,因而疯魔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的电竞游戏和科幻电影,它们与传统几乎已经完全脱离关系了。
至于人文领域中的学术部分,诸如历史学、文献学、考古、考证、乐理等等,则受到后果相反的两种不同影响。它一方面随着崭新技术的出现(例如在海量文献的检索和分析,以及在年代和物质的精确鉴定等方面)而得以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却由于众多新兴学科的出现而不再能够占据学术领域的中心位置,和吸引最优秀人才。两者合起来的结果是,这些领域变为仅由少数学者负责的高度专业化工作,其水平不断提高,在学术文化整体中的影响力却反而缓慢下降。
最后,哲学家是人文学者之中最特殊的人物。他们自认为其所关注的是人类最根本问题,它们历古常新,无所谓进步,但其实许多哲学问题今日已经被学术的进步所跨越。例如,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科学发现,而尚未了解的部分,则绝非可以单纯通过哲学思考来解决。又例如,从二十世纪物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角度看来,洛克、休谟、康德等有关人类认知的讨论其实已经完全过时。此外,当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声势浩大,但它们至终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则恐怕并不乐观。基本问题在于,现代哲学正逐渐蜕变为一个封闭的自足专业系统,因此其冲击力和古代哲学无从相比[57]。在古代,哲学不啻一切学术的泉源。在现代,这泉源之逐渐枯竭到底是由于哲学家对过往问题之执着,还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学术上的进步已经大致穷尽了单纯凭借思虑(而不借助于数学、观察、实验等其它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所能达到的境界?这非我们所能够判断。庄子说得好,“道术将为天下裂”,那么传统哲学是否也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整体看来,日益加速发展的高科技正在迅速改变世界,在其中传统文化并无被抛弃或者消失之虞,而是以各种不同方式被保存下来,成为人类文明的积淀。在此过程中它们无可避免会碎片化,也就是失去了整体的内在联系(例如宗教、艺术、大自然与文学之间的精神相通),而它们的活力与影响力亦在缓慢减退。这其实是文明发展中一个无可避免而重复出现的现象,不独以今日为然。在“轴心时代”哲学思辨逐渐取代原始宗教崇拜(例如颛顼时代的巫觋系统和古希腊的萨满系统)正就是同样性质的转变,虽然如上文已经提及,其过程如今只能够通过考证而得窥一斑了。
人的自由与孤独
“杀死上帝”解放了心灵束缚,同时也消解了人的自我认同与生命意义。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为有尊严,有目标与理想的“万物之灵”,而非浑噩蒙昧与草木同朽的禽兽,是建立在一套传统学说和观念的基础之上,其整体便是所谓“人文精神”。它们在不同文明中有不同表现,但都是经过漫长岁月,千锤百炼,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科学与启蒙杀死了上帝,冲垮了这精神,使它化为零碎片段积淀在文化血脉中,那不啻也摧毁了人的自我形象与认同,亦即人之所以为人的传统基础。因此,正如萨特所宣称,现代人一方面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则变为孤独孑立,无依无靠,必须重新寻找他自己的定位与生命意义,也就是要完全为自己的个人选择负责。很显然,这完全自由的选择又将使得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不同世代都产生破裂,也都碎片化。所以他讲的、面对的是个人,但全人类其实也一样,因为从传统发展出来的个别道德理念,并不足以承担所有国家,亦即全世界的整合原则之重担。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的纷争与财富之所以同步增加,其根源实在于此。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演化已经来到一个巨大转折点,人类今后将走向何方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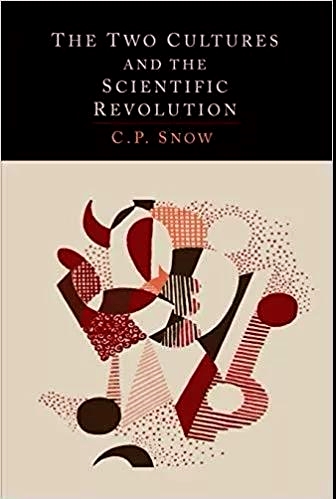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四 人类文明演化的展望
为什么我们认定人类文明现在是处于转折点上?这有许多迹象,例如人类所能够控制和消耗的人均能量之历史性变化,或者地球人口之增长,或者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的普遍趋势等等。但回顾人类进化历史的整体则会带来最开阔的视野,也最能够突显人类文明今日所处的独特历史位置,而这位置与人文精神的前景是很有关系的。
人类进化的回顾
人对本身进化历史获得较为确切了解是相当晚近的事,至今尚不及百年。人类是由进化而来这观念由达尔文在1871年提出,但过了半个世纪方才出现这方面的证据。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和周口店“北京人”的骸骨化石发现于1920年代;最接近人类先祖的阿法南猿和湖畔南猿发现于1970-1990年代;而现代人即“智人”(Homo sapiens)的起源和扩散,则要到1990年代方才由于分子遗传学的兴起而为人所知。现在大致可以确定,人类每一个阶段的进化都是和某些重大发明密切相的。在下表中我们列出这些发明及其所导致变革的估计距今年代,其根据见注释中的说明。

这个表清楚显示的有两点。首先,人类的进化基本上是由技术发明推动(这里所指是广义的技术),每一项重大发明都导致了人本身及其精神面貌的改变,其中最关键的有三项:石器的发明导致早期人类出现,言语的发明导致现代智人出现,农业和文字的发明导致人类文明出现。在中国人观念中,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能够通过文字来发展复杂观念,并藉此相互感染,从而产生“文化”和“文明”,两者都是以文字为根基。西方观念稍有不同,culture和civilization的语根分别是农耕(cultus)和城邦(civitas),其技术和政治意含更重。无论如何,近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是建立在文字、农业、宫室、城邦这几个主要发明之上是没有疑问的。表中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栏所清楚显示的大趋势:从大约一百万年前开始,人类科技的进步开始不断加速,这表现为每项重大发明出现的距今时间大致上以10的倍数递减;到了21世纪,间隔时段已经递减到数十年左右。这趋势倘若持续下去(从今日种种迹象例如5G互联网的发展看来,它的确在持续),那么可以预期,今后改变社会结构的重大发明将不断出现,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正面临整体性的突变(mutation)[63]。它今后到底会发展成何种形态,已经无法预测了。

陈方正《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
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
这个科技的“突变”,可以从它在二十一世纪最初二十年的重大发展看出来,那大致上有三个不同方向的突破:人类基因库、高端智能手机,和阿法围棋。1996年多莉羊诞生是人类复制自然生命的第一步[64],2003年人类基因库(human genome)计划的完成则意味人开始能够解读自身(以及越来越多其它生物)结构之由来,并究诘一切生命的具体运作过程,所谓“生命的奥秘”于焉揭开。2016年面世的阿法围棋(AlphaGo)软件出乎意料之外,打败了所有人类高手,这人工智能研究上的突破意味,某些被认为极高妙的人类思维能力可以被超越,因此人类智能在将来也有可能被复制甚至越过,至于智能机械人逐步取代人类工作则早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当然,这所谓“将来”到底是何时难以确定,大部分人认为当在短短数十年后例如2050年,但坚持即使一两个世纪之后此事也不可能发生的也不乏人[65]。至于2009年出现的第四代(4G)智能手机及其组成的网络所改变的,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系性(connectivity),它使得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幅度侵蚀,由是群体意识日益笼罩、左右个人(在政治、道德、品味等各方面)的判断和选择,商业运作和政治竞争方式亦随之而迅速改变。英美及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政治急速转向两极分化和激烈对抗,也许就是其最明显的征兆之一。
合起来看,以上三个突破所意味的是:科技的飞跃进步正在全面影响和改变人和人类本身。这种影响、改变不一定出于有意识的设计,甚至也不是人所能够完全控制或者了解。不少人天真地认为,科技既然是由人自己研究、发明、推动,其目的就必然是为人类的福祉,倘若它带来意想不到的恶劣甚至灾难性后果,那仅仅是因为思虑不够周详,未能“善用”科技而已,因此当人真正了解这些恶果之后,就必然能够正确驾驭科技,以供自己驱策。例如:能源和资源危机、大自然的污染、碳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等等,都可以通过政策的制订和相关科技的进步来解决。相关的另一个观念是:人有足够智慧来拒绝发展或者使用那些可能导致不可预测后果的科技,例如对物种基因的改造,等等。
这观念表面上顺理成章,但其实未曾触到问题核心,那就是科技发展必然影响和改变人的本身,包括其欲望、观念和意志。所以说到底,科技无所谓善恶,因为随着人本身的改变,判断善恶以及可欲与否的标准也将随而改变,因此科技发展的长远后果是微妙而无法预见或者控制的,过去如此,今日亦如此。更何况,在人类历史上,科技发展一直不可遏止。这是因为它的发展会带来强大能力,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拒绝或者延缓发展科技的国家、社会必将面临淘汰或者边缘化命运。曾经对欧洲咄咄进逼数百年的奥图曼帝国从18世纪开始沦为近东病夫就是最佳例子[66]。即使在世界充分融合为一之后,它的步伐是否可以被控制,其实也仍在未知之数[67]。无论如何,科技持续发展以及它之深刻影响人类本身有其必然性,而不是可以由个人甚至个别社会的主观愿望或者意志所能够改变的[68]。
科技对于人文领域的渗透
上文曾经论证科学与人文领域两者是截然分割的,倘若如此,那么科学的发展又怎么可能如上文所说,改变人的本身,包括其欲望、观念和意志呢?关键在于,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分割虽然深刻,却并非绝对。这可以从科技的影响以及科学对人本身的研究两个不同方面来看。
首先,在传统文化中技术主要依赖经验,与自然哲学关系不大,所以科学与技术泾渭分明,不相牵涉。但现代科学令人能够掌握大自然的根本规律,从而利用这些规律来控制和改变自然;同时这种能力又会反过来,促进科学本身的进步。因此现代科学和技术是互相促进,无从分割的,它们已经融合成为“现代科技”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自然与人的需要、期望密切相关。因此通过“现代科技”的纽带,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已经变得非常强烈。更根本的则是,现代科学本来仅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而不及于高度复杂并具有自主意志的人,所以称为“自然科学”。但今日我们已经普遍接受,人同样是大自然一部分,所以这界线是模糊而且不断改变的。通过生理学、医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现代科技对于“人”本身(包括其生理与心理)的了解正不断加深,对人体的干预也不断扩充和加强,而衔接人脑和计算机之间界面的技术更在不断推进。
那么,自然科学至终是否能够了解和解释人的整体,包括其思想、欲望和意志?生物科技至终是否至终将超越医疗目的而改变人的体质、遗传乃至思维能力[69]?人和智能机器是否将融为一体?这在目前还不清楚,但从其发展趋势看来,则科技对于人和人类整体的了解和影响程度之全面和深刻,恐怕将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在本节开头提出,人类文明正面临整体性的突变,就是基于前面所指出的本世纪三大新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科学对于人本身的理解和干预之不断加深加剧而言。但这个所谓“突变”到底是属于什么样性质的变异呢?这自然无法预知,下面我们只能够作一个大胆的猜测。
人文精神与世界融合
科技的进步使得人本身也能够被客观地研究、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机器更接近于人,而人也更依赖机器;电子网络的发展则使得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照此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是否全人类连同其所发明的智能机器至终将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个人则成为其中一份子,就像生命起源于单细胞生物,它们大量增殖之后积聚、演变,经过多个阶段之后,终于进化成多细胞高等生物一样呢?在未来覆盖全球的“普世人机共生体”之中,是否机器将担负起其躯体的一切功能,个人则蜕变为其思维与指挥中心亦即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呢?这有如科幻小说的场景可能令人发笑——或者悚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已经出现于今日世界了。我们只要稍为想到众多犹如巨无霸的跨国公司的紧密层级组织,或者一支立体化现代军队的繁复指令系统,更不要说一个现代国家的金融、交通、保安等诸多系统的运作和协调,就不能够不同意,它们和有机生命体是颇为相似的。而且,不断发展的科技,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正是使得这样高度紧密、精细、跨越全球的大规模指挥与协作系统得以建立的原因。所以,这样具有特定功能的个别系统至终发展成为“全功能”性质(亦即其在国家范围内高度整合),然后蔓延全球,至终把人类整体网罗进去,恐怕也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浪潮不仅仅关乎制造业、贸易、金融、服务业,更连带关系到法律、环境、卫生标准,所以它就很可以视为这种由科技推动的全面整合趋势之反映。
然而,这个趋势虽然一度似乎势不可挡,实际上还是有很大阻力。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最近数年来出现于欧美的民粹政治浪潮,以及由是而连带爆发的全球贸易战争。它们显示,“人”具有非常强韧的个别性和保守性,那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不同文明所陶冶出来,因此不会轻易被“全球化”逻辑消融。伊斯兰教与西方国家在中东持续不断的猛烈冲突,也同样是这传统与现代,亦即人的保守性与全球化逻辑碰撞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上文提到的人文精神之“碎片化”就不一定是悄无声息的渐进过程,而往往先要经过惊心动魄的惨烈斗争。像西方的启蒙运动,其基础就是上百年的宗教战争,而它本身,又导致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大革命。一个文明的自身蜕变如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当亦不例外。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当科技赋予人类的力量极度膨胀之时,它是否能够转而采取较为理性、平和,不那么玉石俱焚的方式,那无疑就是对积聚数千年文明精华的人类智慧之终极考验了。
人类文明在目前的转折点上还有另一个似乎不那么迫切,但长远而言则更根本,更重大的考验。那就是在科技解决了人类几乎全部需要之后,再从何处为生命寻找意义。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是求生存,也就是求个别人的存活以及人类整体的延续和发展。事实上,所有物种的进化也莫不如此。一言以蔽之,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其终极意义就在于稳定地自我延续,自混沌初开,地球有生命以来的30亿年皆是如此。但言语的发明和智人的出现打破了通过“自然选择”(亦即改变生命的基本结构也就是基因谱)而进化的缓慢方式。文明孕育出现代科技,人类除非愚蠢地自我毁灭,否则其稳定延续的问题在可见的未来就很有可能得以完全解决,亦即所有必要工作都将逐渐为各种机器负担。但届时人的生存意义究竟何在,就要成为严重问题了。
事实上,这问题的迹象目前已经初步浮现了。一方面,简易工作消失,创业致富机会大增,由是造成贫富极度不均,各种社会福利问题成为政治争论焦点,先进国家甚至考虑将普及的基本收入列为国民权利,以求此问题之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厌倦生活,游手好闲,沉迷网上游戏,甚而患上自闭症——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安全舒适环境中成长,没有求生存的压力和磨练。贫富不均问题可以通过社会体制的重新设计而得到解决,但社会过度富裕,令生活失去意义的问题,则是人类文明所从未曾遭遇过的。人文精神是从传统生长出来,它是否能够对这由科技造成的崭新问题提供一些启示,一个新观点呢?倘若人文精神还有能力孕育未来,倘若哲学仍然能够焕发新生命,这应该就是它们的最大挑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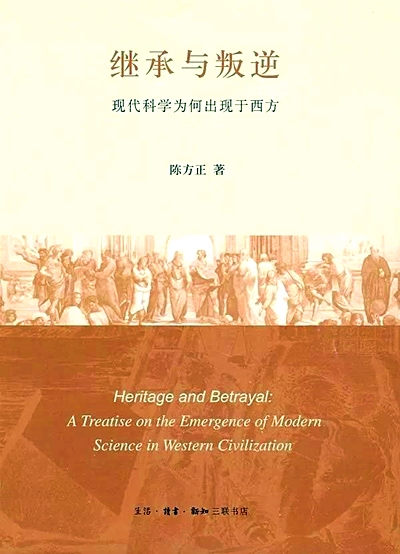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五 结语
在人类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中,由神话、宗教、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交织而成的传统文化一直在进步、改变;同样,支持人类生存、活动的科技也一直在发展,两者的交互影响从未间断。在17世纪以前,科学是这些文化活动中一个独特领域,对技术,对社会整体虽然有影响,却并不很重要。科学革命完全改变了这个形势,它首次为人类找到了了解大自然森罗万象的钥匙,从而导致技术的突飞猛进,后者一方面改变社会的结构及其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协助、刺激科学,使得它能够继续进步,将大至宇宙整体,小至物质最细微结构,复杂如人本身的奥秘逐步揭露出来。
“人文精神”是过去五千年来人类的精神家园。它是用文字,和以文字表达的故事、诗歌、观念、理想等等建筑起来的。它塑造了人类的记忆、感情和欲望,也满足了人类心灵的需求,可以说是和我们所知道的人之为人密不可分。然而,这并非就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的进化,包括现代科技所触发的进化,是无从遏制的,它必然会颠覆传统人文精神所孕育出来的那些人,也就是改变他们的本能、个性、基本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萨特说人没有本质,他完全可以决定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样,但要为此负责,的确是真知灼见。《创世纪》说阿当夏娃因为吃了禁果,所以被逐出伊甸园,也有很深象征意义——人类正是因为吞食了现代科学之果,而失去传统人文精神的乐园,而被迫进入一个陌生的,和五千年来截然不同的崭新世界。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讲的是流水,是时间,但移用于不断改变,不断进化的人类文明和人类自身,也同样是很贴切的。
我恐怕以上这些看法,都不是很中听,也不是许多人,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所能够接受的。但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山崩海啸、天地变色的大时代。我们有足够勇气正视和迎接未来吗,还是会任由让未来淹没自己呢?萨特说得好,这是每个人都要回答,都要向自己负责的。
——2018年6月修订于用庐

【作者简介】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届荣誉院士,港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研院高级研究员。
陈方正,1939年生于重庆,1949年移居香港,1958年赴美留学,先后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届荣誉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哈佛大学、普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物理学学士、硕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自美返港,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从事理论物理和高分子物理研究。1980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秘书长,1986年创办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1990年,创办和主持《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2年荣休,任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2004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2006年荣获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届“荣誉院士”。
陈方正先生的研究范围和学术成就,包括现代化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坎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1984—2000》、《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继承与叛逆》是其标志性著作,内在而具体地响应了“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的“李约瑟问题”,引起学界强烈反响,余英时先生以“体大思精的著作”称许之。
*本文首刊于《中国文化》2019年特大秋季号,凤凰网国学频道受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注释】
[1]指14-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简称“文艺复兴”。欧洲在大混乱时期之后的连串文化振兴运动都称为“复兴”(renaissance),它包括9世纪的“卡罗琳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10世纪的“奥托复兴”(Ottonian Renaissancce),以及12世纪的“早期复兴”,这三者是欧洲文化复兴的初阶,也是此处所讨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基础。
[2]“文艺复兴”的“艺”指大家熟悉的艺术,它开始于十四世纪初的写实风格绘画,后来产生了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众所周知的伟大艺术家。
[3]讨论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是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1860])。有关其中的人文主义有以下大量论述:Paul O.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Scholastic,and Humanist Strains (New York: Harper 1961); Denys Hay,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Eugenio Garin,Italian Humanism: Philosophy and Civic Life in the Renaissance (Oxford: Blackwell 1965); Charles G. Nauert,Jr. (Peter Munz,transl.),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有关其对日后欧洲影响则见Wallace K. Ferguson,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Five Centurie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48).
[4]奥古斯丁的《上帝之都》便是此类论争的最重要典籍之一,其中对新柏拉图主义有详细论述。
[5]此为关键阶段,其完成经过见下列巨著:Pierre Riché,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Barbarian West,Sixth through Eighth Centuries. John J. Contreni,transl. (Columbu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6).
[6]有关北意大利城邦的兴起见下列著作:J. K. Hyd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Italy: the Evolution of the Civil Life,1000-1350; Daniel Waley and Trevor Dean,The Italian City-Republics (Harlow: Longman 2010).
[7]有关公证人体系与人文主义的密切关系分别见下列论文集及巨著,后者对人文主义的兴起有极详细论述:Ronald G. Witt,Italian Humanism and Medieval Rhetoric (Aldershot: Ashgate 2001); The Two Latin Cultur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in Medieval Ita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8]有关的作家例如阿尔拔坦奴(Albertanus of Brescia,c. 1200-1270)、拉提尼(Brunetto Latini,c. 1220–1294)、马萨图(Albertino Mussato,1261-1325)等均出身于公证人世家,见上引Witt的两部著作。
[9]有关佩特拉克,见Ernest H. Wilkins,Life of Petrarc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受早期拉丁文作者影响的,还有伟大诗人但丁,但他的《神曲》以意大利方言撰写,观念、情怀则以基督教理念为依归,所以与人文主义无涉。
[10]有关14-15世纪人文主义发展的专论见George Holmes,The Florentine Enlightenment,1400-1450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92);讨论布鲁尼共和思想的专书有Hans Baron,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有关人文主义学者家世、事迹、关系、交游见Lauro Martines,The Social World of the Florentine Humanists 1390-146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有关波吉奥的大发现见Stephen Greenblatt,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NewYork: Norton 1992)。
[11]有关人文主义如何散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即英法德荷诸国见Charles G. Nauert,Jr.,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Ch. 3。
[12]有关伊拉斯谟见下列传记:Léon-E. Halkin,Erasmus,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1987);讨论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关系有下列论文集:Donald Weinstein,ed.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1300-160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13]有关蒙田见Marvin Lowenthal,ed. & transl.,The Autobiography of Michel de Montaig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6)。此书是编译者辑录和翻译大量有关其生平的蒙田文献与书信而成,书前的导言亦是一小传。
[14]见前引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其主要论点便是文艺复兴运动对于基督教思想造成沉重甚至致命打击,例如它断言(见该书p. 370):“这样,获得拯救的需要在意识中就越来越淡薄,同时现世的进取心和思想或则全然排除有关来世的一切思念,或则将之转变为诗意而非信条的形式。”这观点引起极大反响和争论,百年不息,但只是被弱化和修订,而始终没有被否定。见Philip Lee Ralph,The Renaissance in Perspective (London: Bell & Sons 1974),Ch.1。
[15]以下概述主要是根据余英时以下两部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篇(台北允晨2003);《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台北允晨2004)。
[16]分别见上引《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三章与第八章。
[17]相传陈抟生于唐末,活了118岁,这似乎难以置信。倘若以他在后唐长兴三年(932)到洛阳应试时最多五十岁来推算,则生年当为882年,也活到107岁。
[18]根据余英时,新儒家的发展经过了韩愈的“古文运动”、王安石的“新学”,以至二程的“道学”等三个阶段。但王安石并不排斥佛教,对此二程深为不满,认为是大害。见上引《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三章,特别是第73-87页。
[19]他们重视《中庸》,是因为其与佛教的“中道”接近,智圆更自号“中庸子”。见上引《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四章,特别是第124-137页。
[20]见上引《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297-332页。
[21]当然,全面感染中国不止佛教,而还有起源于本土的道教。但道教本是众多本土崇拜的合称,并无精深教义或者成体系的组织,它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受其刺激方才多方模仿佛教并且采用老庄哲学为其内核,从而发展成为高等宗教的。因此我们在此不再分别论述道教。
[22]有关存在主义的论述和著作浩如烟海,简单介绍见Steven Crowel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xistent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Walter Kaufmann,From Shakespeare to Existential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Ch. 10-11;文献摘录见Walter Kaufmann,ed.,Existentialsi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New York: Meridian 1956)。
[23]存在主义有许多不同向度,例如其现象学(phenomenology)传统,那以黑格尔、海德格、萨特的著作为骨干,或者其对生命态度的论述,特别是承担(commitment)、真实性(authenticity)、面对死亡等观念,这以加缪(Albert Camus)为中心。我们在此的讨论仅以存在主义有关宗教方面者为限,而并非对其整体作一均衡论述,读者鉴之。
[24]中文译名亦作齐克果或克尔凯郭尔。
[25]见Miguel Unamuno,The Tragic Sense of Life,J. E. Crawford Flitch,transl. (New York: Dover,1954),pp. 305-306。
[26]“God is dead!God remains dead!And we have killed him!” 见Friedrich Nietzsche,The Gay Science. Josefine Nauckhoff,trans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Section 125.
[27]该演讲后来翻译成英文出版,见例如Jean Paul Sartre,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Philip Mairet,transl. (London: Methuen,1948);中译本见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8]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29]当然,这些也就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像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美国要到最近才经过艰苦政治斗争而建立起来。
[30]见前引One-Dimensional Man,p. 257。
[31]无论在政治评论抑或语言学,乔姆斯基都著作等身,有关评论也浩如烟海。从《二十一世纪》(香港)双月刊所刊乔姆斯基专辑,包括访问、介绍、评论和短传,可以对他得到初步了解。见该刊第28期(1995年4月),第4-27页。
[32]Harold Bloom,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1994).
[33]见上引Western Canon,pp. 517-519。
[34]这部巨著随即引起一场有关文化传承与开放社会理念(也就是各种新兴社会力量与新兴学术观念进军学院所产生的冲击)之间的大辩论,其各种观点可从以下论文集见一斑:Jan Gorak,ed.,Canon versus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Garland 2001)。
[35]其它流派尚包括: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守旧派;受哈佛大学白璧德(Irving Babbit)影响的梅光迪、吴宓等学衡派;纯粹的传统文化发扬者钱穆;以及致力于振兴佛教的杨文会、欧阳竟无、太虚法师等。
[36]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谭嗣同《仁学》、章太炎《訄书》等皆出版于1897-1901年间。
[37]关于杨文会、南条文雄以及日本与中国佛教在近代的复兴,见葛兆光以下论文:“日本东本愿寺与中国近代佛学的因缘”,《二十一世纪》第33期(香港1996年2月),第29-41页;“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的佛学兴趣”,《二十一世纪》第45期(香港1998年2月),第39-46页;和以下专著:张华《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教思想转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Chan Sin-wai,Buddhism in Late Ch’ing Political Though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pp. 69-72,此书主要讨论谭嗣同,但也涉及杨文会、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除了欧阳竟无以外,另一位振兴中国佛教的重要人物太虚法师(俗名吕沛林,1890-1947)亦曾短暂师从杨文会。
[38]关于马一浮,见滕复《一代儒宗——马一浮传》(杭州出版社2004)以及吴光主编《马一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9]马一浮颇有意在此书院恢复古代理念,但抗战时期经费短绌,人才不济,熊十力应邀来讲学又因办学方针相左而离去,所以书院开办后其实只有一年半时光就陷于停顿。
[40]景海峰的《熊十力》(台北东大1991)是一部深入的学术传记,对熊的思想发展有详细阐述和扼要分析。
[41]此书有三个不同版本,其内容观点一直有变化,分别出版于1923,1926和1930,最后一版名《唯识论》。
[42]此书激起了佛学界特别是欧阳竟无、太虚法师及其弟子们的一再反驳,以及熊十力一方的辩护,争论持续十数年,至大陆解放后方才逐渐歇息。该书的语体文版在1944年出版。
[43]梁漱溟有下列传记: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马东玉《梁漱溟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Guy S. Alitto,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44]有关唐君毅见张祥浩《唐君毅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第一章“唐君毅的生平”,并参见牟宗三、徐迂等著《唐君毅怀念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有关牟宗三见颜炳罡《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45]见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54)。
[46]见利瓦伊武《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47]四人《宣言》发表于《民主评论》1958年元旦号,钱穆受邀联署但拒绝参加;徐复观驳斥胡适的文章“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载《民主评论》12卷24期(1961年12月20日),此文发表后仅两个月胡适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民主评论》由徐复观等于1949年在香港创刊,1966年停办。
[48]要从“仁心”来建构复杂的现代世界,特别是产生科学体系与民主意识,显然非常困难。为此牟宗三提出“良知的自我坎陷”这个特殊观念。姑无论其是否能够成立,这样的尝试也洵足令人惊佩了。
[49]另一方面,颇堪注意的是:有大量研究和证据显示,无论在东西方,古典文明却又都是从更原始的宗教中生长出来,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2014)以及Eric R. Dodds,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50]斯诺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The Rede Lecture系列讲座中提出此说,见C. P. Snow,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51]当然,传统文化中的法律、建筑、工艺、医学等属于实用范畴的学问也是显著的例外,它们在前现代可以视为广义的“技术”,到了现代则成为实用科技的一部分,这将在下文论及。
[52]在今日看来这很自然,因为宗教是应人的需要而生,因此“人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神”;甚至入世的儒家也同样可以有宗教性,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一文,载所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第31-98页。
[53]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之后,人类许多固有观念例如时间、长度、因果、物质本性(例如质点和波动的分别)等等都已经被完全颠覆,而不复能够为一般人所能够充分了解了,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精确意义必须通过数学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54]当然,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是显著的例外,它仍然是英国建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议会的贵族院享有法定议席,在国家大典中也继续发挥重要功能。
[55]有关这段历史及相关讨论见本文作者的三篇论文,收入陈方正《现代世界的建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113-194页。
[56]当然,如所周知,印度教目前颇有由于政治原因而进入建制的趋势,那和本世纪初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重新崛起十分相似。至于其它东南亚佛教国家如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等都经历了激进政治革命,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复杂,但大体上也类似土耳其的情况。另一方面,佛教在泰国历来是建制一部分,这关系至今未曾有根本改变,佛教地位仍然相当稳固。这独特现象当与泰国历史以及其政治形态密切相关。
[57]唯一例外也许是在哲学边缘的数理逻辑,那对于计算器科学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科学哲学、环保哲学、医疗哲学等等的兴起也是个新趋势,但它们深度不足,并不能够融入正统哲学主流,而往往变为个别社会问题的批判和讨论。
[58]原则上人类起源是以人和猿的分支为准,那是个尚未完全厘清的复杂问题。我们姑且以1990年代发现于肯尼亚的湖畔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nanmensis)为标志,它大约出现于4Mya(百万年前),早于1970年代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南方古猿(A.afarensis)。湖畔南猿的形态接近能人(Homo habilis),但是否为其直系先祖尚未确定。
[59]最早的旧石器出现于2.6-1.8Mya的奥杜威(Oldowan)石器技术,其标志是粗制的石核与石片,能人的出现大约与之同时,这被视为从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进化到人类(Homo)的转折点。见李浩“阿舍利技术与史前人类演化”,《科学》(上海)第71卷第3期(2019年5月25日)第10-14页。
[60]早期阿舍利(Achulean)石器技术以剥取大型薄石片来制造灵巧工具为标志,它出现于1.76Mya,直立人(Homo erectus)的起源稍早,大约为2.0Mya,后者的特点为身高已经与现代人相若。见上引李浩文。
[61]人类最早控制用火年代约为1.2-0.7Mya,那是从南非岩洞遗址中烧焦兽骨和经煅烧石器的年代推断,见Francesco Berna et al,PNAS(US) May 15,2012 109(20)E1215-E1220。具有阿舍利石器技术的直立人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最早是在1.5-1.4Mya,但规模很小,第二趟大规模扩散则是在0.8-0.6Mya左右,见上引李浩文。此外陕西公王岭蓝田人的年代已经被重新定为1.63Mya,“北京人”(周口店直立人)的年代被复位为0.75Mya,不过他们到底是从非洲扩散抑或是从本地进化而来则未有定论。见朱照宇等“中国黄土高原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记录”以及吴秀杰“中国发现的重要直立人头骨化石”,分别载《科学》(上海)第71卷第3期(2019年5月25日)第15-19页及20-24页。
[62]乔姆斯基认为言语的发明是人类进化中一个突变过程,出现于0.20-0.08Mya之间。见Robert C. Berwick and Noam Chomsky,Why Only Us: Language and Evolution(Cambridge: MIT Press 2016),pp.149-150。至于智人(Homo sapiens)大约在0.3-0.2Mya出现于非洲,大约在0.10-0.08Mya向全世界扩散,则经过最近大量基因遗传学的研究,已经是公认事实,而这与言语发明的关系显然非常密切。
[63]这大趋势以数学形式表达是Tn = T0 10-n ,其中Tn 是用火知识发明之后的第n个重大发明的距今时间,T0是百万年。从此可以推断,倘若以百万年前为起点,那么在其后重大发明出现的频率ρ将循下列形式爆炸性上升:ρ = 1/(T0 –t),其中t是自百万年前起计算的时间。因此当t接近T0(即目前)时ρ将趋于无穷。当然,这只是个归纳出来的现象规律,不完全准确,但它的确显示,人类当前已经处于技术变革的所谓“奇点”(singularity)。
[64]这个突破当时导致了一位这方面专家详细探讨和热心推动克隆人体以及创造“超级人类”的可能性。见Lee M. Silver,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Avon Books 1997)以及笔者的下列书评:陈方正“伊甸园能重整吗?论现代人焦虑的根源”,收入《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坎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450-466页。
[65]有不少资深科学家持此等意见,他们或则以本身的超卓智力来考虑此问题,或则因为专业造诣很深而对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持过分保守态度。这令人想起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始终不以为然,或者路透福特坚决认为原子能的应用为虚妄。但科学进步的界限和步伐不可能从先例来判断或预测,因此他们的看法是否正确也只能够留待后人回顾。
[66]见前引笔者在《现代世界的建构》中的三篇论文。另一个绝佳例子是德川幕府在统一日本之后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刻意令本来在16世纪就已经蓬勃发展的先进枪械制造工业萎缩以至消失,因此当美国海军在19世纪闯开其国门时,日本人已经不知火枪为何物,以致完全无法抵抗。见Perrin Noel,Giving Up the Gun (Boulder: Shambala,1980)。
[67]将近百年前,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其著名科幻小说《美妙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中就已经预言,未来人类社会将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将禁止科学研究。见该书第16章。
[68]有关此问题的论述参见陈方正,“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论人工智能与未来世界”,载《科学》(上海)2017年第5期17-23页。
[69]见前引Remaking Eden一书的预言与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