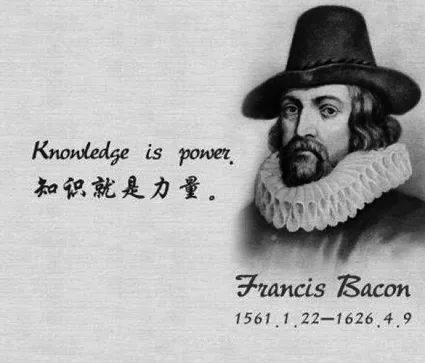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并不是这么说的
培根(资料图)
人们总是说,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其实,培根并不是这么说的,他的原话是: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Knowledge and human power are synonymous)。
这句话出自培根的哲学著作《新工具》(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4年10月版,许宝骙译)第一卷第三条语录。循着书中译注,还能找到关于“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的若干衍生表述——
这三种发明(印刷、火药和磁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而说到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全靠方术和科学了。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第一卷第129条语录)
虽然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路途是紧相邻接,并且几乎合二为一,但是鉴于人们向有耽于抽象这种根深蒂固的有害的习惯,比较妥当的做法还是从那些与实践有关系的基础来建立和提高科学,还是让行动的部分自身作为印模来印出和决定出它的模本,即思辨的部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两条指示——一是属于行动方面的,一是属于思辨方面的——乃是同一回事:凡在动作方面是最有用的,在知识方面就是最真的。(第二卷第四条语录)
显然,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就是力量”,是对培根在《新工具》中一系列论述的浓缩并格言化的结果。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将这顶知识史上的语言桂冠戴在培根头上。
对知识史进行考察,人们有理由认为,是弗朗西斯·培根重新定义了“知识”。因为培根,人类的知识,即对世界的认识、对自然的探究,被截然分为两个阶段——他之前的和他之后的。
培根言说的知识,一如《新工具》书名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声称人类要运用知识支配自然、对万物建立统治的,不乏其人。但少有人像培根这样如此鲜明地提出:有用的知识才是真知。
有用的真知从何而来?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之《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培根认为,从实践(验)中来。培根反对那种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所谓知识,他把实验观察、事实积累和生活常识引入了认识论。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支撑了培根的抱负。《新工具》第一卷开宗明义:“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依照书中的观点,知识源自实践,又将付诸于实践;它既是先前行动的总结,又是后续行动的法则;它是经验的,而非超验的。
《新工具》堪称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开篇宣言,知行合一这篇宣言的基调。从“知行合一”的模板上拓印出“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乃至“知识就是力量”,是逻辑的必然,是语言在某种思想法则框定下的填空。
经验主义者,在思维模式上天然倾向于归纳法。因为基于感性经验的认知,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总是习惯于从具象的、特殊的而非抽象的、一般的方面着手。培根《新工具》的“新”,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所强调的演绎法的扬弃。
《新工具》
作为新工具的归纳法的提出,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英伦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分野。培根之后,两种思维模式塑造了所涉人群不同的哲学观念、行为方式、法律体系、政治风格和社会经济风貌。而培根之前,溯源欧洲哲学史,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思想类型也长期处于相互对立、斗争,又彼此交叉、渗透的状态。两种思想类型的纠缠,始于米利都学派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万物之始为何的认识分歧。此后,经历了普罗塔哥拉感觉经验说与苏格拉底天赋观念论的对立、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反映论与柏拉图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而亚里士多德,则摇摆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并实现了两种思想倾向的调和,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进入中世纪后,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在经院神学内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抗仍以“唯名论vs唯实论”的形式延续着。直至近代,哲学终于摆脱神学的羁绊。与此同时,科学也逐步从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于是,培根全新知识观的提出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梳理认识论的发展,因为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对抗、论战的大背景,可以发现,人们对知识本身的态度也不尽一致。相对而言,经验主义由于坚信通过经验可以洞悉自然奥义,注重感觉的作用,所以更侧重于知识的功能属性;而理性主义由于笃信唯有理性才能把握事物本质,注重心灵的力量,所以更强调知识的伦理价值。譬如,苏格拉底就曾探讨过“美德即知识”的假设,柏拉图则阐述了“一切知识都是灵魂回忆”的命题,而亚里士多德又有“学问是富贵者的装饰品,贫困者的避难所,老年人的粮食”一说。
《工具论》
上述三位古希腊思想家,除了亚里士多德带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相调和的痕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属比较纯粹的理性主义者。所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论及“知识”大都与“美德”“灵魂”之类的词汇挂钩,而亚里士多德所言“学问”则多少有了些功用的属性。
人们可以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构成培根哲学体系重要的思想源流。然而,单论培根的“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很难说他们给予培根何种提点或启发。事实上,查阅古希腊罗马的相关典籍,对“知识”的论述中未见有与“权力”或“力量”相捆绑的句式。可以这么说,如果要为培根的名言找一句“前世”,它应该不在古希腊罗马一脉。
那么,作为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基督教文化中,是否有与“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类似表达?
《圣经》是人们必然会想到的文本。从“知识”的视角看待《圣经》,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还是吸纳融汇了近东和欧洲社会早期历史、文化和哲学的文献汇编,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作为“智慧之书”的《圣经》,有不少关于知识和智慧的论说。在《圣经·旧约》中就《诗歌智慧书》五卷: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其中,箴言一卷里有大量关于人生哲理的探讨,“智慧”是串联此卷各章节的关键词,如“智慧的赏赐”“智慧的高超”“智慧的呼召”等等。箴言卷,就是一本高浓度的智慧语录。例如:第二章的“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第八章的“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第16章的“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而在箴言卷第24章中,有一个让人眼熟的句子: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
“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与培根所言“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尽管句式有差异,但都表达知识与权力(力量)的关联。前者比之后者,在含义上甚至更接近于广为传播的“知识就是力量”。
人们无论多么艰深的思考,都是在诉说着古老的命题。培根又何尝不是?或许,他并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