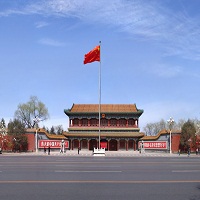「学思平治」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独家抢先看
★★★★★
2001年春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一些参加“断代工程”的学者积极向科技部建议,支持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2001年底,科技部决定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预备性研究。这项先后作为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研究,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到今年春季已经进行了整整20年。这20年间,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参加工程的近20个学科(几乎涵盖了所有自然科学一级学科)的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拟对工程的宗旨、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和取得的成果进行阐述,以就教于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各位同行。
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背景与缘起
(一)20世纪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
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大量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郭沫若等通过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结合古代文献研究古代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端。20世纪80年代,在浙江余杭良渚[1]、辽宁喀左牛河梁[2]、安徽含山凌家滩[3]、山西襄汾陶寺[4]等遗址,先后发现了社会分化严重的墓葬,其年代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早于夏王朝建立的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引发了中国考古学者和古代史学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
1985年,夏鼐发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5],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利用考古资料,直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稍后,苏秉琦根据相继出土的与文明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提出了各地文明起源 “满天星斗” 说[6]和 “古文化、古城、古国” 以及 “古国、方国、帝国”[7]一系列关于文明起源的观点。他们的研究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严文明[8]、张忠培[9]、李伯谦[10]、李学勤[11]等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组建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课题组,把各地研究文明起源的学者组织起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掀起了高潮。[12]他们循着文字、冶金术、城市等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 “要素” 开展研究,其中关于礼制的出现及其与文明起源关系的研究颇具特色。[13]
及至20世纪末,中国史学界大都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中华文明的肇始,把距今5000多到4000年期间的社会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这一千年的社会究竟是处于哪个社会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关系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脉络的认识,是一个亟待研究和科学论证的问题。
在20世纪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存在一些突出的共性问题,比如缺乏对文明形成标志的研究。及至20世纪末,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学或考古学者的个人研究,十分缺乏同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尤其是缺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对作为文明形成重要基础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生业的发展、手工业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发展变化及这些因素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状况分析,缺乏对某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整体研究,对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少有深入探讨,也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较少涉及。更缺乏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对比研究,这使得中国学者不仅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缺乏话语权,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权威阐释。
二 宗旨与特点、主要研究内容
(一) 探源工程的宗旨和特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进行科学研究与论证,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与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其多样性的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14]为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探源工程的研究,要尽可能全面地研究各方面的因素站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不同于以往进行的专题研究,需要做到两个结合:
第一,考古学与古史传说和文献历史学的结合。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对的问题。历史学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历史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包括王朝世系、社会的组织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背景,这些对于通过考古资料研究当时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考古学为历史学提供的则是历史文献中较少或阙如的过去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然而,这些实物资料大都不能直接和古代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相联系,需要对这些实物资料及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进行阐释。这就需要参考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或古史传说。中国文明起源于尚无即时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它的追溯探讨,不得不依靠考古学的进展,这就格外需要将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相结合来进行研究。
第二,促进考古学与各种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
大量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是探源工程最大的特色。根据研究的需要,近20个自然科学学科的数十种技术与方法被用于工程各个课题的研究。运用加速器质谱仪对出土遗物进行高精度碳十四测年;运用硅酸盐技术研究陶器和原始瓷器的烧制工艺技术;运用金属学的方法,对出土铜器的金属结构和成分以及制作工艺技术进行分析;通过人骨中包含的碳、氮同位素研究当时不同地区人们的主食种类(粟和黍还是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蛋白质的摄入量;通过动物遗骸和骨角制品,探讨不同地区人群的肉食获取方式、动物资源的驯化与利用方式;通过人体中所含的锶同位素,研究当时人们的迁徙;通过土壤中粒度、磁化率、孢粉、植硅体、土壤微形态等对各个地区的环境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各地文明的盛衰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地貌学与遥感技术对各地区遗址的地形地貌和古河道走向等进行考察;通过对各地墓葬出土的古代人骨观察,研究当时人们的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对各地出土人骨的DNA进行分析,研究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与迁徙;对与天文学有关的遗迹研究,探讨当时的人们对天文现象、方位和农事节气的知识;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对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聚落的分布状况进行研究,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对遗址出土的动物和植物遗骸进行分析,研究各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基础;运用地质学、材料学的知识,分析铜器、金器和玉石器、绿松石等贵重资源的产地。
(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20世纪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探源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以下重点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1.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突破以往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 “三要素” 或三条标准,根据中国的材料,归纳出通过考古资料辨识文明形成的关键特征。
2.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探讨各地史前社会从平等的、简单的氏族社会发展演变成为以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国家为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时间和演进过程。对中华文明来说,国家起源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核心问题。[15]
3.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探讨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文化的互动关系,各地区的文化和区域文明是如何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的,揭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相互促进、碰撞融合、汇聚一体的演化历程,以及各区域的文化或文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4.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及其作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境外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联系,这些联系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5.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研究中华文明是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或因素有哪些;这些动力或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彼此之间有何内在联系;通过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并进而探讨导致这些特点和道路形成的原因。
简言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研究中以各地区都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为核心,兼顾社会各个阶层,讨论国家的起源和王权的出现与强化过程,运用多学科手段探讨文明起源过程中各方面的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动态描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样态。
三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框架、环境背景与生业基础
(一) 通过高精度测年,准确把握了距今5500到3500年我国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各个都邑性遗址及其他区域性中心性遗址的年代
探源工程设立了年代课题组,在20世纪末实施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 对夏商周王朝年代进行系列测年的基础上,运用AMS(加速器质谱仪) 测年技术对全国各地距今5500至3500年期间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测年标本进行了系列高精度测年。经过15年的努力,测年课题组共测了数千个标本,得出了全国范围内距今5500到3500年期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并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对应的年代关系;解决了距今5500至 3500年期间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包括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为研究各个地区的文明进程、关键节点的年代,以及各区域之间相互关系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年代学基础。
(二) 初步探明了中华文明演进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针对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中缺乏环境研究者的加入,致使各地区文明的兴衰与环境的关系扑朔迷离,难以确定的状况,探源工程专门设立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关系课题。环境课题组通过开展对各个区域距今8000到3500年期间环境的研究,对各区域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背景及其与文明盛衰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16]
距今8000到6000年期间是全球范围的大暖期,气候整体上温暖湿润,为世界各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距今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于今天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于今日的华南地区。正是由于较好的自然环境,促使各地区农业显著发展,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对各地的环境变化的研究发现,环境的变化确实对各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距今4300年到4100年期间,曾经发生了较大范围的环境变化,对各地区文明的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以长江下游为例,一度十分繁荣的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左右发生衰变,都城废弃,人群流离,以居住在良渚古城中的最高统治者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崩塌,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衰落。通过工程设计的环境变化与文明关系课题的研究,我们得知,良渚文明的衰落与环境的变化对其稻作农业造成严重影响密切相关。在良渚古城繁荣的时期,面积广阔的低湿地被开垦为稻田。由于距今4400年前后的洪水频发和地下水位上升,这些曾经作为水稻田的广大区域重新沦为沼泽。良渚古城周围古城衰落时期地层中,禾本科花粉显著减少,与古城兴盛时期的禾本科花粉浓度极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良渚文明晚期稻作农业遭受了致命性打击。由此可见,适宜农业发展的环境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距今4300年前后环境的变化使得农业受到严重打击,是导致长江下游区域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17]
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文明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长江下游地势低平和单一的水稻种植相比,多样的地形条件和粟黍稻豆等构成的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体系,使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应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三) 系统地考察了各地区文明形成的生业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往往忽略对各区域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的考察。针对这种情况,探源工程专门设置了生业与技术的课题,多学科结合,系统考察各个区域距今10000到3500年期间,特别是距今5500到35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并探讨其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确实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
在距今10000年前,在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栽培水稻。农业的起源,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状态奠定了基础。
在河南新密李家沟等遗址,发现距今万年前的小型定居村落,出土了初期的陶器和细石器。[19]在距今9000至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取得发展,人口增加,村落的数量和面积有所增加,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丰富起来。
在距今8000到6000年期间气候整体温暖湿润的环境下,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种植粟和黍,同时兼种水稻。河南舞阳贾湖发现距今8000年的村落,[20]遗址面积5万多平方米,发掘出数十座房址和数百座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炭化稻和迄今年代最早的家猪。居住址和公共墓地内墓葬的规模及随葬品显现出差别,少数墓葬规模比一般墓葬略大,随葬绿松石装饰,有些墓主人腰部随葬多件内装有小石子的乌龟壳,有的龟甲上有刻划符号,有些符号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似。有些墓葬中出土用鹤类翅骨做的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不等,共数十件。研究者对其中一件七孔笛进行了测音,发现音阶准确,至今可以演奏乐曲。[21]上述这些发现说明当时淮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饲养家猪,制作多样陶器、石器和骨器;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很丰富,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了掌握刻划符号及制作和吹奏骨笛的人,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分化的端倪,已经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长江中下游地区始终以水稻作为主要的农作物。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10000年前已经开始水稻的栽培。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经营早期稻作的定居村落,出土了水稻的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22]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上山文化晚期的聚落和墓葬,出土石器和制作精美、表面涂红衣的陶器,有些陶器表面还用白彩绘出太阳纹、点线纹、平行短线等纹饰,[23]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审美和信仰方面取得的进步。到了距今8000年前,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浙江浦江跨湖桥遗址出土了长达5.6米的独木舟,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近海航行的能力。[24]这几处遗址的居住址和墓葬看不出明显的贫富贵贱的差别,当时的氏族社会还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到了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多个遗址发现了当时的水田,稻作农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为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9000到8000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取得初步发展,出现了周围有围沟的定居的聚落,[25]史前文化取得发展。距今7000年前,形成了高庙文化。以白陶和表面刻圆目、大口、獠牙的兽面形象为代表的陶器反映出当时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26]
在长城沿线与西辽河流域,粟作农业在距今10000年前后也开始兴起。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栽培的粟和黍。[27]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围沟聚落。聚落内发现成排分布的房址,出土了炭化的粟和黍,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还有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和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28]在部分房址内居住面以下发现了墓葬,部分墓葬随葬陶器和制作较为精致的玉玦、玉坠等装饰玉器,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琢玉工艺技术。有一座墓葬随葬一雄一雌两口家猪,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开始出现贫富分化的端倪。
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进一步发展。[29]有人质疑当时各个区域农业是否取得了发展。我们认为,农业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取得了进步。在长江下游地区,大约距今55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犁耕;到了距今5100至45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多次出土了石犁及其他耘田器等多种稻田农具;在良渚文化之后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水田中,还发现了水牛的脚印,可知在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犁耕已经比较普遍,稻作农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农业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应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只是这方面的表现在考古资料上往往难以辨识。长江下游浙江茅山遗址特别是余姚施岙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的水田,稻田规模达10万平方米 (相当于14个足球场),田埂、沟渠很规整,显然早已超过稻作农业初期小规模水田的阶段。在良渚古城内中部的莫角山高等级建筑区附近,出土了大量炭化稻谷堆积,估计总重量逾20万斤之多,这也证明良渚文明兴盛期稻作农业确实比较发达。
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乃至剩余价值,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给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一是人口的显著增加。距今6000年以前,聚落分布较为稀疏,村落的规模大都是数万到十几万平方米,多者不过几十户人家。距 今6000年之后,聚落的数量较此前显著增多,聚落的规模也明显扩大。二是早期城市的出现。这一时期开始,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规模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表明出现了人口的聚集,形成了早期的城市,成为当时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在一些等级高的早期城市中,出现了布局规整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和有丰富随葬品的大型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日益明显的贫富与贵贱的分化。这些变化应是在适宜的环境下,农业得以显著发展,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探源工程手工业课题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各地史前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工艺技术也取得了进步,最为突出的变化是,高技术含量、高等级的珍贵物品(如玉器、精致陶器、漆器、绿松石装饰品等)工艺技术生产专业化的出现。如辽河流域牛河梁大型积石墓和长江下游地区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的高等级墓葬随葬的玉人、玉龙、玉鸟、玉龟;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明的玉琮、玉璧和玉石钺以及各种玉饰。良诸古城大墓出土的玉琮,在一毫米的宽度内有五到六条刻线;黄河下游地区的厚仅不到一毫米、薄如蛋壳的蛋壳黑陶;黄河中游地区陶寺文明的龙盘、鼍鼓、石磬、玉石钺和各种彩绘漆木器和铜器的制作;石峁古城的铜器和玉器制作以及精美的石雕技术等,无一不是当时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的表现。这些工艺的技术含量较高,需要专门的工艺和技术,绝非每家每户的居民都可以胜任的,说明当时各地出现一批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家族,世代传承,才得以取得如此高超的技艺,制作出精美绝伦的产品。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应是出现社会分工的表现之一。
这一时期,各地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技术含量高、制作精致的物品都出于各地高等级的墓葬中,表明各地权贵阶层已经掌握了这些贵重物品的原料供给、生产和分配。考古发现,中心聚落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到社会成员中的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也即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由此可见,高端手工业为权贵阶层所掌控,应是各区域文明演进的共同特点,也是首领的权力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
四 探源工程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探源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5800至4000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这些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以下一些共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口显著增加,社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出现了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说明出现了人口向政治中心集中的现象;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掌管集团公共事务的管理阶层和掌握军事指挥权力的首领,以及琢玉、制骨、冶铜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工匠家族;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贵贱分化,社会财富被权贵阶层和家族所占有。与此同时,各个区域发现的此阶段的遗址,表现出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
大约5800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30]、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的几万平方米大小的普通村落。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 “邦” “国”,兹称之为古国。而自大约58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 “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31]
学界对古国和古国时代的称谓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学者主张就古国的社会发展程度而言,相当于当代西方学术中通用的 “酋邦” 概念,不如照搬,且方便和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而我们主张使用 “古国” 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承袭了古人的称谓,因而具有传统特色,还在于古国这种社会基层结构自产生以来一直延续到三代,即 “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 (《战国策·齐策四》) 是也,其间的演进变化十分复杂,远未厘清,但却是理解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之所以采用这个称谓,实际上还有为了将来随着对其研究深入,可能揭示出更多中国上古历史特点特色内容以及提炼相关理论而预留空间的策略方面的思考。
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
在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数个年代在距今5800到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同时期的中小型聚落。其中,北阳平遗址和五帝遗址面积都是70多万平方米。经过大规模发掘的西坡遗址的围沟聚落内面积为40万平方米。[32]遗址周围有用作军事防御宽达10米的围沟环绕。在遗址中心部位有一个广场,围绕广场有四座大型建筑址。基址的室内面积达240多平方米,连同室外回廊等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这些大型建筑建造得十分考究,它们应是该大型聚落中权贵人物居住和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公共墓地,其中27号墓长5米、宽3.5米,墓主人为青年男性,规模比一般氏族成员的墓大数倍。墓中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和十余件陶器。从墓葬的巨大规模和随葬玉石钺来看,墓主人可能是居住在这一聚落中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首领。随葬的十余件陶器烧制温度较低,显然不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器,而是为了随葬而特地制作的 “明器”,这是在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年代较早的为了随葬而制作的 “明器”。这座墓葬的规模虽然大大凌驾于其他一般成员的墓葬之上,但与墓葬的规模相比,墓内随葬品并不算丰富。这种情况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成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化具有不同的模式,中原地区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即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时期,是以首领居住址的规模和墓葬的规模彰显自己的地位,而并非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尊贵。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还处于分化的初期,集团首领还没有凭借手中的权力将社会财富据为己有。
如此规模的大型聚落以及数量众多的大中小型聚落聚集在一起的现象是此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未见的。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人口显著增长并异乎寻常地集中于此地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活动的区域内,在被认为可能是黄帝炎帝集团兴起的时间段,出现了大型聚落集中分布的情况,令人深思。
距今53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地区西部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似乎暗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此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33]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遗址现存面积 117万平方米。在最内侧环壕以内,用围墙环绕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间区域内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共有三排,中间一排面阔五间,两侧的房屋基本对称分布,面阔三间,总面积约2400多平方米,且布局已经呈现出中轴线理念的端倪。在这组建筑群以南,发现了规模更大的两座单体巨型建筑基址,面积分别为1600和1300平方米。
双槐树遗址的布局和高等级建筑的规模与河南西部铸鼎原遗址群的西坡遗址四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周围的布局迥然有别,显示出全新的布局理念,高等级建筑群位于聚落北部正中,几座建筑同一方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递进。这种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排列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意义深远。
遗址围沟内发现了四处公共墓地,墓葬头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几处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四处公共墓地中,有两处墓地的中部各有一个方形夯土台,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祭坛。在距离高等级建筑最近的一个墓地的祭坛附近,发现数座规模明显大于一般小型墓的墓葬。
双槐树大型围沟聚落,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现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较之于距今5800到5500年期间铸鼎原遗址群所看到的状况更加严重。因之,李伯谦最先将这一阶段的黄河中游地区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称为 “河洛古国”。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经历了8000年前农业的初步发展,人口繁衍,出现了定居聚落,精神文化方面取得显著进步;6000年前,社会出现明显分化,出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和面积达数百平方米,制作考究的大型建筑以及比一般社会成员的墓葬大数倍的大型墓葬,但是随葬品的多寡并无明显差别,也看不到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与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同时期大型墓葬中随葬大量精致的随葬品和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迥然不同,暗示出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和模式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以青台遗址出土了丝织品的残片,双槐树遗址出土用兽牙制成的家蚕形饰为代表,说明当时中原地区已经能够养蚕和缫丝。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34]该遗址发现距今5800到5500年崧泽文化的村落和公共墓地。这里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公共墓地。几座大型墓集中在一个区域,周围有数座中型墓,与其他小型墓分布区域显著分离。大型墓内随葬多件制作精致的武器——玉石钺和玉玦、玉环、玉坠等装饰品,以及数十件陶器,而为数众多的小型墓不仅墓圹狭小,而且随葬品也往往仅有两三件日用陶器,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发现反映出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明显的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显贵阶层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财富,其社会贫富贵贱分化的严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是十分突出的。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距今5500到5300年左右,年代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相衔接。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安徽南部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遗址分为贵族墓葬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大、随葬品十分丰富的高等级墓葬。等级最高的墓葬随葬品多达数百件,以玉器为主,有多达数十件的玉石钺和数十件玉石锛铺在尸骨上下,还有玉人、玉龙、玉鸟、玉龟等,随葬品总数达300多件。大量玉钺暗示出当时的首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反映出宗教色彩。16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祭祀区和墓葬区反映出严重的社会分化,权贵阶层可能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通神祭祀的权力,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到达或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6000年,出现了迄今国内年代最早的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城址呈圆形,面积约9万平方米,周围有宽数十米的壕沟。城内发现巨大的祭坛、建筑基址、道路和完整的排水系统。该城址被连续使用了近2000年。[35]
辽宁省喀左牛河梁遗址群位于辽宁西部的丘陵地带。[36]在这一地区,发现了距今5500至53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遗迹群。在40个大大小小的山头上,都发现了用石块修筑成圆形的祭坛和方形的积石墓。大型积石墓随葬玉龙、玉龟、玉鸟等动物形玉器和玉璧、玉玦、玉镯等装饰品,个别墓葬还随葬玉人。在一处较高的山头上,用石块砌筑出一组面积达 7万平方米的巨大平台,应是举行祭祀等大型仪式的场所。在该大平台同一山头的南坡,有一个形状特殊的建筑,里面有数量众多、大小不等的泥塑女人像和龙、熊、猛禽泥塑的残块,还出土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女人头泥塑像,这里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的一处神庙。由于牛河梁遗址群一带一直没有发现居住遗迹,所以,这里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专门埋葬贵族和祭祀神灵的原始宗教圣地。最近,在朝阳半拉山遗址发现了一个红山文化的积石墓地和祭坛,出土了数件石人头像,最高达40厘米,再一次印证了红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37]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阶级分化,可以葬在牛河梁圣地的人应是地位特殊的权贵阶层。他们的墓葬中只随葬精美玉器,不见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具,这些不同种类的玉器真正用于装饰的较少,也少见武器,多是玉人、玉鸟、玉龟、玉璧等具有宗教色彩的玉器,或暗示出当时的权贵阶层掌握了祭祀权力,即与神沟通的权力。崇尚神灵,权贵掌握通神权力可能是该地区权力出现和文明演进的突出特点。
(二) 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
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历史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突出的变化是在一些地区,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位于浙江北部余杭的良渚都城遗址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为了防止这座建于沼泽区域的城址遭到城址以北丘陵地区洪水的侵害,在筑城之前,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集中了周围广阔地区的大量劳动力,利用自然地势的起伏构筑起长十几公里、高数米的多段水坝,整个水坝分为高、低坝系统。[38]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一水利系统除了防范洪水对古城的侵害之外,还可能具有在不同水位期蓄水,用于灌溉稻田的功能,库区面积相当于两个西湖。在修建巨型古城之前,良渚社会的统治者还组织劳动力,在城内中心位置堆筑起长630米、宽450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足球场),高近十几米的高台。在高台上,修建出多组高等级建筑群供权贵阶层居住。又以高台为中心,在周围修建起南北1900米,东西1700米,城墙墙基宽20—150米,高约4米,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 (相当于4个北京故宫)。内城的城墙墙基宽达40到60米,先用从别处运来的石块铺垫厚度0.5米做墙基,石块墙基上用其他地方运来的黄土堆砌成数米高的城墙。在内城城墙之外,有宽数十米的壕沟。
内城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内城之外利用部分自然山势,结合人工堆筑,修建成面积达620万平方米的巨型外城 (相当于8个故宫)。经过估算,修建城内高台、内城、外城和巨型水坝的工程量十分巨大,约需要3600万个劳动日,如果动用10000劳动力连续工作,也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仅仅依靠良渚古城内及其附近的居民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显然是动员了归其统辖的相当广阔地域的人来共同参加这一超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由此可见,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已具有非凡的动员和组织人力的权威和能力。如果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不是国王依靠国家的力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居住遗址和墓葬的规模、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等方面都清楚地反映出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贫富贵贱的差别。高等级建筑建在人工堆筑的巨大高台之上,单体建筑面积达二三百平方米的多座建筑周围有围沟环绕;高等级的墓地位于专门砌筑的大型祭坛之上,一座墓葬往往随葬近百件器物。其中最高等级的王墓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玉璧、玉琮。这些玉石钺和玉琮、玉璧只见于大型墓葬中,应是彰显持有者拥有军事权力和主持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权力,这些玉质器具应是尊贵身份和祭祀神灵的器具——礼器。在江苏南部的武进寺墩[39]和苏州草鞋山[40]、上海福泉山[41]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中,也发现文化面貌相似,随葬多件玉璧、玉琮和玉石钺的高等级墓葬。
上述这些现象揭示了良渚国家的基本面貌: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级差明显的社会阶层的分层。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行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褫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有高规格宫殿建筑,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关系展开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所以在城内发现的大规模粮食仓储和大量居民所需粮食消耗皆需外来供应,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在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存在高度一致的、具有强烈的 “一神教” 特点的宗教信仰,而在人类宗教发展史上,一神教是晚出的宗教形态——如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且它们的产生通常伴随了民族、国家的重大变故,换言之,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宗教中心和贵族手工制造业中心,统治者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控制了长江下游 (今日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 的广阔区域;在其他地区如今天的上海、苏南等地还有若干次一级的地区中心,它们结成网络,实现对文化全域的控制,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和一些次中心构成,以及众多中小型聚落构成组成的多层级的、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稳定的控制区域的社会管理体系,说明这时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42]凡此种种,都反映出良渚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这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良渚古城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是千真万确的。
在同时期的江汉平原,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43]城内有祭祀区,出土数千件红陶杯、大量小型的陶塑人像和动物塑像,整个城内原始宗教色彩浓厚。
澧阳平原的澧县鸡叫城遗址,从距今6000多年的小型聚落,到距今5000年前形成一座城。[44]近年,在城内发现一座大型楼阁式建筑基址,基址底部有大型木结构的垫板做基础。基址本体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回廊,总面积达630平方米。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三重环壕,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型聚落。聚落内发现大量炭化谷糠堆积,推测稻谷总量达22万公斤。
由良渚文化率先开启的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浪潮波澜壮阔,又此起彼伏。大体而言,与良渚文明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地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史前时期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该地区的社会分化十分严重。20世纪60年代前半,在泰安大汶口遗址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中,发现墓葬规模明显大于一般社会成员,墓内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大型墓葬。[45]近年,在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和滕州岗上遗址,都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公共墓地。在焦家遗址的一个墓葬区域,埋葬着多座高等级墓葬。墓地坐落在人工堆筑的土坛之上,大型墓葬不仅墓圹规模大于一般墓葬,而且使用木质棺椁,有的使用两重椁和一重棺。这几座大型墓的墓主人都是青年男性。每个大墓中随葬几十件制作精美的陶器,还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表明墓主人掌握军事指挥权。他们很可能是军事首领。[46]在最近发现的滕州岗上墓地,四座并列的男性大型墓随葬300多件精致陶器,每个墓葬还随葬大小两把玉石钺。[47]这两处墓地的大墓中的随葬品比小型墓多数十倍,表明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贵贱的分化,社会财富被权贵阶层所掌控。在焦家和岗上遗址,都发现同时期的大型中心性城址。
值得一提的是,海岱地区最先发明了用木质棺椁做葬具和陶鬶、陶盉等带有三个空袋足的陶制酒器,这些因素被中原地区集团所吸收,成为当地棺椁葬制和陶制酒器的组成部分。后来,根据陶制酒器发展而来的铜盉、铜觚等青铜容器,成为夏商周时期表明贵族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
(三)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
距今4300—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叫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此间的变化首先是在大格局上,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相反,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这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郫县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陶寺城址的使用年代约距今4300到4100年。城址长1800米,宽1500米左右,总面积近280万平方米,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48]高等级建筑区位于城内东北部。单体建筑基址面积最大者达8000平方米,基址附近出土陶瓦和表面涂有白色和蓝色的刻划墙皮,说明当时的高等级建筑相当考究。宫殿区周围有围墙围绕,形成中原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最早的宫城。在陶寺城址早期的大墓中,随葬近百件随葬品,其中有表明墓主人尊贵身份的鼍鼓、土鼓、石磬、龙盘和表明持有者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而同时期的小型墓基本上没有任何随葬品,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极为严重。在陶寺都邑最为兴盛时期的大墓中,带有精致漆木柄的6件玉石钺沿墓壁摆放成一排,应是为了彰显统治者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具。墓中还随葬数量众多的漆木器、玉器。在这座大墓的旁边,发现了一座半圆形,由外向内逐渐升高的坛状遗迹,内层的夯筑围墙上特意留出20道缝隙。天文学家认为,这个遗迹是根据太阳从位于遗址以东的塔儿山上升起,阳光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到人工夯筑的圆心点来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49]有些学者认为,陶寺城址的年代、所处位置、城址规模和等级等方面都与文献记载尧所居都城——平阳相吻合。
及至21世纪初,陕北地区的史前社会演进一直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十年来,芦山峁遗址与石峁巨型史前城址的发掘,使该地区成为研究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热点地区。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碾庄乡,[50]大体也开启于距今 4300年前后。该遗址面积达80万平方米,是这一时期陕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大营盘梁位于芦山峁遗址的核心区,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垫土夯筑而成的巨大台基,长160米,宽100米。在台基的顶部呈 “品” 字形分布着三座院落,一座大型院落位于北部正中,其南部两侧是两座面积在700平方米的小型院落。一号院落为前后两进的四合院式建筑。在院落内中部偏北处,并排分布着3座主体建筑,每间 200平方米,建筑之间有宽3米的过道。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筒瓦和板瓦,与陶寺遗址共同把我国古代开始使用瓦的历史提前到4300年前。在这组建筑的南端有一小型广场。芦山峁遗址大规模的聚落体量,特别是 “宫殿” 式建筑群落的出现,显然是当时陕北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居所或祭祀场所,标志着当时这一地区社会分化已相当严重。
陕西神木石峁巨型城址的年代约距今4100至3800年,是一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用石块包裹土芯砌筑的山城。[51]该城址由外城、内城和皇城台构成。皇城台位于城内高处,可以鸟瞰全城。城墙自下而上分为多层砌筑,现高十余米,气势恢宏,显示出居住在其内的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尊贵身份。皇城台内有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宽阔的广场,和通向城内的高大门楼和道路。近年,在砌筑皇城台台基边缘墙体的石块中,发现了雕刻出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有的纹饰与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十分相似。遗址还发现了高一米,直径数十厘米、雕刻兽面图案的石柱和十多件鹰形的陶制品。石峁遗址发现的大墓由于被盗,墓中随葬品所剩无几,但仍存有殉人。从内城、外城和皇城台的宏大规模看,城内最高统治者的大墓应当是有丰富随葬品的。在一些中型墓葬中,出土了铜齿轮性腕饰等铜制随葬品。这座依山而建的城址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外城和皇城台城门附近,都发现用于阻止敌人进攻的防御设施——瓮城,外城城墙外侧还设置多处突出于城墙外侧的附属设施——马面和位于转角处的角楼等防御设施。这一发现将这些防御设施开始出现的年代较原来的认识提早了两千年。此外,在皇城台、内城和外城城墙的石块缝隙中多有玉器发现,被认为是希望借助于这些玉器所具有的 “神力”,阻止外来入侵者。石峁遗址的一系列发现表明,距今4100年前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在晋陕高原和河套地区,在石峁城址存在的时期,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石城,规模大小不一,年代基本相当,体现了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的文明演进道路。从已发掘的山西兴县碧村[52]、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53]等城址来看,这个地区内大型聚落、中型和小型聚落中,都有一个类似石峁皇城台的高级核心区域,只是因聚落不同,其核心区的大小各异,在小型聚落里,也许只是众多窑洞簇拥的一座石砌建筑院落而已。这种情况似乎意味着晋陕高原的石城聚落的建造依据了统一的设计蓝图,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的特点。因此,当时应当存在一个以居住在石峁古城的王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和早期国家。有迹象表明,可能正是石峁集团的南下,导致了陶寺古城的衰落。
古国时代晚期,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无疑是其都城。夏鼐早就指出,二里头已经不再是初始形态的文明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是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五 根据中国的实际材料,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新标准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 “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晚期开始,只有3300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界,往往根据史书中关于 “禹传子,家天下” 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当以开启了世袭制度的夏王朝为肇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 “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哈拉帕文明的图章并没有被学术界认可为文字。追溯 “三要素”的由来,我们发现这 “三要素” 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基于这样的认识,工程从实际材料出发,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头等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一) 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工具种类,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例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比较普遍地使用了犁耕,并发明了多种稻田中使用的生产工具。从比良渚文化更早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水田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水田规模很大,灌溉系统比较完备,早已超过了小水田的阶段。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在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可以想象,除了生产工具之外,在生产技术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能一味强调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发生重大进步,从而否认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农业取得的发展。例如,不能因为在各地发现的汉代的铁质生产工具在种类和形制方面都和近代的同类农具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化,就因此得出两千多年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没有很大进步的结论。因为农业的发展,除了生产工具之外,还有良种的培育、施肥、中耕等,各个环节取得的进步都会促进农业的发展。
(二) 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取得显著进步。在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技术工艺高超,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乌黑发亮,最薄的器壁只有0.3毫米。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的制作工艺技术十分精湛,如在反山墓地等级最高的,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良渚 “王墓” 的反山12号墓出土的形体最大、制作最精致的“玉琮王” 表面的人兽合体的 “神徽” 图案,在一毫米的宽度内有五条刻线,其工艺的精湛可见一斑。这些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确实出现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成为彰显持有者身份的礼器,所以,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 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早期城市
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繁衍。在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的非自然原因的集中。在一些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其特征是,聚落规模巨大,面积达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前述的良渚、陶寺、石家河、石峁、二里头都是如此。
(四) 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
社会分化严重,出现少部分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成了具有某些高技术含量或资源稀缺的贵重器物——礼器,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至于这些礼器的种类,则因地而异。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中,贵族墓葬中随葬可能具有祭祀功能的玉琮、玉璧、三叉形器和表明掌握军事权力象征的玉钺。良渚城址反山12号墓内随葬多件玉石钺和一件制作精致带有短柄的权杖。在陶寺遗址的大墓中,随葬陶鼓、木鼓、石磬、龙盘、玉石钺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礼器。在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高等级墓葬中,是制作精美的陶制酒器和玉石钺以及多重木质棺椁。
(五) 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
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王和高级权贵们居住的大型高等级建筑 (宫殿)。良渚、陶寺、石峁遗址莫不例外。进入夏王朝以后,二里头遗址 “多宫格” 围垣布局中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54]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六) 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
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都邑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城市。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墓葬位于公共墓地的一隅,单独成为一个墓区。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就位于由上万座墓葬构成的公共墓地中的一个区域,该区域由几座大型墓和几十座中型墓构成,不见小型墓。到了陶寺城址兴盛时期,大型墓脱离了公共墓地而位于南城墙附近用围墙围绕的一个单独的区域,附近有数座中型墓,应是大墓墓主人的亲族。单独构成王族墓地的还有良渚古城,在古城内城内外,发现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几个高等级贵族墓地,说明良渚的王及其亲族的墓葬已经脱离了公共墓地而被单独埋葬。
(七) 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1.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良渚时期罕见的有人殉的墓葬。赵陵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台状土山,东西长110米,南北宽80米,呈椭圆形,占地1万平方米,高出四周约9米,周围有古河道环绕。20世纪90年代前半曾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以良渚文化为主的墓葬94座。[55]按墓主贫富贵贱分区埋葬,并有规模较大的集中杀殉现象,杀殉人数中有半数被砍掉下肢或双脚,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乃至夏王朝之前全国范围内所罕见。石峁遗址的大型墓葬中在墓主身侧往往有殉人。还有些遗址发现有人被埋在大型建筑的基础中作为奠基。山西陶寺遗址宫城中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基础内就发现人骨和动物骨骼。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曾发现多座人头坑,个别人头坑内曾埋有24个青年女性人头骨。这种奠基、杀殉习俗一直延续至晚商时期。[56]在殷墟的大型墓葬和建筑内,都有作为牺牲的人群。这些被杀殉的人不大可能是墓主人的亲属,而很有可能是战俘,或是生前因犯罪等原因成为供墓主人役使的奴婢。
2.战争频发。自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各地的墓葬出现随葬武器——石钺的现象。陶寺遗址的一些青年男性的墓葬中,常可见到随葬一件石钺。此外,这一时期的墓葬中石镞和骨镞的数量明显增加,且镞的体量增大,杀伤力增强。[57]在各地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且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可以认为是彰显墓主人掌握了军事指挥权。随着战争的频发和规模逐渐扩大,掌握军事权力的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手中的军事指挥权发展成为主宰日常社会生活的王权。
(八) 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各个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域。这一区域中的人们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这一区域内的不同小区域存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王的都邑为中心,形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虽然官僚管理机构不容易在没有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但进入文明社会的各个区域无一例外需要有官吏作为维持王的统治的保证。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兴建、陶寺和石峁古城的兴建和维持社会生活的运营,仅仅依靠王是绝对做不到的,都离不开为王服务的官僚机构。
我们提出的从考古发现中辨识文明产生的标志,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国家的出现除了通过当时的文字资料证明之外,很多是需要通过考古发现的遗存去辨识的。国家出现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出现了国王,即王权的产生。而王权的产生,是会在考古发现中留下痕迹的,这就是:1.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2.作为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3.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大墓;4.表明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礼器和礼制;5.战争和暴力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标志既适用于中国,也符合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是探源工程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六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机制的认识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 仰韶文化彩陶的扩展
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的以花和鸟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逐渐施加影响。此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所及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有学者认为,形成了 “文化上的中国”[58](的雏形——笔者按)。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应当是炎黄集团兴起,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强烈影响的反映。
(二) 距今5500年左右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 (古国文明)。她们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辉,似百花绽放,争奇斗艳。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此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
1.龙的形象的出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约6000多年的一座墓葬中,在人骨架的旁边,有用贝壳堆塑的龙和虎形象,[59]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龙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贝壳堆塑的龙在东,虎在西,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神思想的方位恰相吻合,应非偶然,暗示着四神思想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安徽凌家滩和辽宁牛河梁墓地的大墓中,都出土了呈C形的玉龙。山西陶寺遗址早期大型墓中都随葬一件绘有彩绘盘龙纹的大陶盆。[60]到了夏代后期的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用两千多片绿松石镶嵌在有机物上形成的龙形饰物。[61]商代晚期的王——武丁的妻子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带有龙纹的铜盆。可见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2.从 “以玉为美” 到 “以玉为贵” 的理念。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玉环等距今9000年的玉质装饰品;[62]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少数墓葬中,出土了制作较为精美的玉玦和玉坠等玉制装饰品,[63]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 “以玉为美” 的观念。到了距今5500年前,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除随葬 C形玉龙之外,还随葬各类制作精美的玉器。体呈 “C” 形的玉龙、玉鸟和玉龟的形态,特别是两地出土的玉人姿势都是双手并拢捧在胸前,非常相似。相聚数千里之遥,却存在如此相似因素,不可能是巧合,说明当时中华大地各个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存在着信息的交流,由此导致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而这正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3.海纳百川——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如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特点的陶鬶、陶盉、陶觚等陶制酒器、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土物相同的双翼形玉饰、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小麦栽培、黄牛和绵羊的饲养及冶铜术等,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积极吸纳周围各个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呈现出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黄河中游地区的汇聚。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积极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4.辐射四方——中原地区夏文明对周围广大地区的文化辐射。进入夏王朝之后,特别是夏王朝后半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原与周边的交流从尧舜时期以对周围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和汇聚为主,转变为以对外辐射为主的模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面积达360万平方米,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从遗址的年代、规模和位置判断,它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宫城以南,发现与宫城仅一路之隔,同样以外墙围绕,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生产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青铜容器和绿松石装饰品。[64]说明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使之成为维持其统治的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后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的先河。
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确立的时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得以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出现了大型玉石钺、玉刀、玉璋、高领玉璧等,具有表示持有者高贵身份的大型仪仗用具,初步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夏代后期重要的仪仗用具之一——玉璋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流域乃至中国香港和越南北部都有发现,[65]表明夏代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进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具体体现。
七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如前所述,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另一方面,在其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过交流。大约距今5000年前,发明于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66]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67]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68]在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也是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首都——安阳殷墟。[69]上述外来文明因素的融入,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逐步形成了粟、黍、稻、麦、大豆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猪、狗、牛、羊、马的家畜饲养体系。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的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经过创新,发明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器,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70]马和马车的传入,丰富了黄河流域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大约也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从西亚传入我国境内的同时,原产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栽培也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地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也说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断,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加以吸收和创新,是以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八 结语
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全国同行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取得了显著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背景、原因、机制与动力,对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理事会大会上,良渚古城和水利设施被批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理事会对良渚古城的入选原因做了如下阐述:“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进入文明阶段得到了世界遗产界的认同。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探源工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道路、各个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模式、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相关的文明的内在特点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缺乏对其他古老原生文明充分的了解,缺乏比较研究,影响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分析。特别是由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还没有系统地向学术界报告和缺乏对全社会的广泛深入的宣传,致使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历史真实” 的认识尚未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学者坚持认为良渚、陶寺、石峁遗址所处的社会是处于 “部落联盟” 阶段,中华文明始自夏王朝建立。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国文明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而且中国版图内的文明,是分布于青藏高原以下遍及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总面积至少25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体量之大,为同时期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对这其中的各支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概括,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 “多元一体”。而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将这些地方文明视为个案,分别就其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又是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结出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果。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2020年开始,“探源工程” 开始了第五阶段的实施。项目负责人和团队也做了调整充实。我们相信,在几代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机制,她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必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参考文献略)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