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越光|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


独家抢先看
我和汤一介先生相识于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半期,当时我是《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为我们新创刊的《走向未来》杂志(季刊)去找汤先生约稿。第一次共同工作是1989年在北京香山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中国文化书院、北京二十一世纪研究院(《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转向实体化的机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共同发起,研讨会的六次全体大会,分别由庞朴、陈方正、金观涛、赵令扬、汤一介、陈越光主持。而在1991年8月,我被汤先生吸纳到中国文化书院担任副院长,这一任职持续三十年之久;2022年2月起,我担任院长。所以,我想从“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的角度来谈谈汤先生的事业与人生[1]。
一 评价汤一介的四个维度
汤一介(1927-2014)是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关于他的生平简介在网络和媒体上已比比皆是。现录2014年出版的《汤一介集》(全十卷)中的“作者简介”作为概括[2]:
汤一介,1927年生,湖北省黄梅县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儒藏》(精华编)、《中国儒学史(全九卷)》等。
这份简介应是汤先生最后审定的自我介绍,出于学人自谦,没有提及所获荣誉,如曾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孔子文化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3]。
评价汤先生的生平所为,可以有四个维度:教学生涯、学术著述、编纂出版和社会事业:
第一,以在北大带研究生为主线的教学生涯。汤一介1951年1月在北大提前毕业,分配至北京市委党校当教师,五年后调入北大,此后就一直执教于该校,1985年晋升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至2014年去世从教逾六十三年[4]。汤先生培养的学生一些已成为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坚,如景海峰、杨立华、强昱等。
第二,以专著《郭象与魏晋玄学》为代表的学术著述。汤一介的学术著作涵盖了道家道教研究、儒家思想、佛教与佛教史、哲学方法论探索、跨文化学的建构诸方面,反映其著作全貌的是2014年出版的《汤一介集》,而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既是汤一介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他个人学术思想的代表作。论者指出,“这本着作除了深入到郭象思想的内部去处理‘性分’‘独化’‘儒道关系’等复杂面向之外,还成为这个时期全面确立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路径的‘方法论’读本”[5]。
第三,以编纂《儒藏》为代表的学术文献整理出版。汤一介的编纂出版甚丰,仅2000年以来,就主编八卷本的《国学举要》丛书、十四卷本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九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以及四十卷本的大型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组织编辑出版了七卷本的《汤用彤全集》,等等。而汤先生倡议并主持《儒藏》编纂,更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学术文化工程——儒家文献的整理、编纂与研究。目前,《儒藏》精华编已经完成,我们可期待全本《儒藏》的面世。2024年9月9日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上,时任《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的李中华评价道:“古代大贤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三者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就《儒藏》的编纂,于立言说,汤先生诚可当之乎!”

第四,以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的社会事业。80年代以来汤一介从事的社会事业众多,但开始最早、影响最大、历时最久;共同发起并成为代表人物,关键时刻因他而存,因他而持续发展;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就是中国文化书院。这对汤先生本人及其开展的其他方面事业都有影响。他开创的许多文化机构都与书院有关,如他创办的北大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就长期与书院“两位一体”。他主编的许多丛书是在书院组织,他发起编纂《儒藏》最早的倡议和讨论,也是在书院内部进行的。
二 评价80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的四个维度
二十世纪先后有两次文化思想运动成为热潮,引发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热切关注、投入。第一次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的伦理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为标志,第二次是80年代的“文化热”,以新启蒙和文化反思为主潮。回顾80年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时,人们常把1984年1月出版第一批书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同年12月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6月出版第一批书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三个团体,并称为推动“文化热”的“三驾马车”。这几个团体思想倾向上各有侧重,但都着眼于从五四往前走,都着眼于中国的现代化。

评价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文化热”中的作为,可以有如下四个维度:
第一,开创民间文化讲习。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后举办的第一项大型活动,就是1985年3月4至24日举办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共二十讲。首讲由沉寂了三十年的九十二岁传奇学者梁漱溟先生开讲“中国文化要义”,其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侯仁之、金克木、虞愚、牙含章、吴晓铃、戴逸、何兹全、阴法鲁、朱伯昆、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杜维明、陈鼓应等著名学者陆续开讲。听课学员二百余人,来自全国各地,每位学员缴纳听课费200元(人民币,下同)。1985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为673.2元[6],200元是当时一个中国城镇居民近四个月的生活费!四十年前的这次讲习班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历史开创性。形式上,这是约三十年后重新开启了民间性社会讲学,今天社会培训、办班讲课已成为巍巍壮观的一大产业,源头可追溯至此;内容上,这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结束后,第一次大张旗鼓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宣讲,今天的国学研究、“国学热”也可以寻此历史性重聚大气之源。此后,书院的各种办班不断,仅1985至1986年间有档案数据留下来的就有十二个班,而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为期两年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注册学员共12,754人。后来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郭齐勇、陈卫平、贺卫方等著名教授在80年代都曾是书院的学员。1989年8月2日中国文化书院毕业典礼上,汤一介以这样一段话送别这届函授班的学生:“让我们永远记住马克思的教导:只有那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的人,才能达到那光辉的顶点。”[7]


第二,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在“里通外国”作为一顶政治帽子的阴影刚刚挥去不久的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就喊出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口号,在80年代的民间文化团体中,中国文化书院的国际学术活动、学者交流是最多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型会议如“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与北京二十一世纪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1989),与美国新基督教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研讨会(1989),等等;二是邀请或接待境外、国外的学者来华讲学、访问交流,如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杜维明、林毓生、成中英、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等著名学者。据不完全统计,书院仅1987年就邀请和接待国际及境外学者32人(其中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来两次,合计为33人次),包括美国12人、新加坡7人、日本4人、澳大利亚2人、加拿大1人、意大利1人、香港4人、台湾1人;三是安排导师出去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讲学,如鲁军1987年去日本参加“国际形而上学会京都会议”,启功、黄苗子1988年赴港讲学,庞朴同年去美国参加“民主与社会正义:东方和西方”国际会议。

第三,组织学术编撰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各种文化讲习班期间,编撰自印教材十五种、600万字,自行刊发《中国文化书院学报》、《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资料》和《中国学导报》(虽几次向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申请公开出版刊号,未果),其中《中国学导报》1987年已向十九个国家的1,100个研究机构和学者寄送。书院设立了出版部、发行部和编译馆,制定了“中国文化书院文库”五年规划(1987-1991),分论著、演讲、资料、译文、古籍、教材六大系列,计划出版一百种学术著作。1988年8月,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组织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为学者出版个人全集之举亦具有开创性,1989年5月正式出版第一卷,至1993年6月八卷出齐,共524.5万字。书院编纂出版了110万字的《中国文化研究年鉴(1989年)》,填补中国年鉴出版史上的一个空白,汤一介说:“从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我们编成了这本《1989年中国文化研究年鉴》,它是迄今为止第一本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年鉴。”[8]

第四,建立独立民间机构。中国文化书院是80年代全国性文化团体中唯一完成机构、经营、管理实体化的,它在1984年首先注册成立了企业法人机构,然后又成立书院并以“挂靠”方式获得办班许可和机构合法性。先于它成立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于1988年开始实体化机构建设,但未能完成;后于它成立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也未实体化。这也是1989年下半年《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停止出版后,“三驾马车”只有中国文化书院能存续下来的重要因素。1987年书院登报招聘全职员工,应聘者竟有1,600多人,许多是自愿放弃体制内工作来应聘的,200人入选面试,选出46人参加培训,最终录用30人;书院1987年度自营收入303万元,新增固定资产45万元,结余136万元。这样规模的民间文化机构,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书院在80年代创建独立民间机构的创新与探索、遇到的问题与挑战、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民间社会组织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
三 中国文化书院对汤一介意味着甚么?
讨论“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当然要问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业对汤一介意味着甚么?他对此事有怎样的认定?作出怎样的付出?又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看汤先生本人的“认定”。80年代以来,汤先生除了北大校内任职外还有众多的社会兼职,如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什剎海书院院长等学术文化机构的领导职务。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只是他众多兼职之一吗?汤先生晚年回顾时说:“我先后做过不少民间学术文化团体的负责人。但只有中国文化书院是我全心全意为它尽力的,这是我自己的事业。”[9]“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汤先生心目中对中国文化书院在他人生中的位置认定。而外界认定和他的自我认定也是一致的,例如《汤一介学记》中约三分之二的追忆文章都特别提到汤先生创办中国文化书院[10],可见在学人的心目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与汤一介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在80、90年代,“汤一介的文化书院”,几乎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别名。
其次,看汤先生对此的“付出”。汤先生在不同文章中多次说到他的学术研究是在80年代才真正走上正轨的,如此算来,在汤先生的学者生涯黄金时间中,为中国文化书院付出时间最多,承受的责任、风险和委屈也最多。责任上,当了整整十六年院长、法定代表人,尤其1989年后的十一年,从方向把握到内部管理,从资金筹措到大项目实施,汤先生处处操心,事事担责。风险上,1990年初至1993年10月间,书院未获注册登记,实际处在“非法”状态,汤先生不得不顶着法律风险,一边开展文化项目,一边四处联系挂靠以取得合法身份。承受委屈上,既有80年代末书院内部分裂,汤先生被无端攻击,受到威胁;又有90年代为书院获得注册登记四处奔波而遭受的冷遇,为筹资遇到的出尔反尔。为了中国文化书院,凡此种种,汤先生都一一承担了。
再者,事业与人,从来是互相成就的,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业,对汤先生又有怎样的“影响”呢?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开展书院的事业,使他不自限在书房和讲台,而是立足于大时代下搏击进取大潮流的大平台,书院导师队伍汇聚了国内外几十所名校名所的十几个学术领域顶尖学者,这对汤先生此后全球化视野和学术领域扩展、学术和文化事业组织,包括倡导并主持编纂《儒藏》都有实际影响。可以说,此举奠定了汤先生从北大名教授到学界领袖的基础。学界领袖地位,有的是因开创学科的学术建树,有的是体制授予的特殊位置,而汤先生是在跨校际、跨专业的学术活动组织中被认可的。
另一方面,在操持办中国文化书院这件“难事”上,也成就汤先生“事上磨”的锤练。汤先生为人谦和包容,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汤先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和,他总是温文尔雅,总是谦和平静。另外,做学问和当老师,汤先生也有诸事亲力亲为的习惯。但做事,就得用人,就会有容用舍留之择;做事,也总要有进退行止的拿捏,甚至不得不有怒目金刚之断。
我举两个例子:1993年,我要辞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汤先生希望我仍挂着副院长,“没有精力可以不常务”。我觉得不妥,约了汤先生和孙长江一起谈,我提出不挂副院长,以利风气。老孙同意我的意见,说“越光不会假客气,挂这个副院长也不能给他增加甚么”。老孙被称为书院的“军师”,一般非学术事务,汤先生多是尊重老孙意见的。但这次汤先生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深思熟虑地提出四点:“一我们是朋友;二你是在书院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书院的,我总希望我们俩合作搞书院;三以后书院还需要你支持;四你一撤会有些人有想法或想进或想退,会不稳定”;“日常工作可不过问,但大活动仍能参加”。此后,他还专门给我写信说明他的这些意见。这就有了我挂这个副院长三十年后,面临是否接任院长的犹豫时,乐黛云先生一句“你不接,就对不起我们老汤了!”的棒喝。
另一件事是1997年10月,中国文化书院接待一个号称“世界儒学研究促进会”的访京团,某会长信誓旦旦地当众宣布要每年捐10万元给中国文化书院,“请汤院长笑纳”,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不认账了。汤先生并没有一笑了之,而是直接收回给他的顾问聘书,并以个人名义给每位当时在场者致信,通报彼“有背于‘诚信’精神”,“很难再进行合作”[11]。为此等事,本非汤先生所擅,然身在其位,事不避难,在书院这件“难事”上,磨砺了汤先生用人处事深谋远虑、当断则断的领导者意志品质。
四 汤一介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影响
“欧盟之父”莫内(Jean Monnet)的名言——“没有个人就没有开始,没有组织就没有持续”(Nothing is possible without individuals, but nothing lasts without institutions),深刻揭示了社会变革与事业创建中个人创造与组织化力量的互动关系。我尝试从“个人—开始”和“组织—持续”两条线,来看汤一介对中国文化书院事业的作用和影响。
建立中国文化书院最早的酝酿,起于1984年3月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鲁军创办民营公司或民间教育团体的一个设想。鲁军找到同事李中华、王守常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青年编辑田志远等商量筹划、各方联络,在这个阶段汤一介并没有参与。8月汤一介从夏威夷开会回来,他们联系上汤先生并推举他出面主持。此后的整个筹备期,无论是“中国文化书院”名称的确立、高规格发起人和创院导师队伍的组成,还是为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与教育部及北大领导会商,汤一介都身在其中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当然,推动事业“开始”的“个人”,未必只指一个个人。没有汤一介还会有中国文化书院吗?也许还会有,但必定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书院,无论其内涵、其规格、其规模、其持续性。
在1984年12月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至1988年的创立与发展期,汤一介作为书院院长,对外是书院的代表人,是重大活动的主持人;对内是书院老中青三代学者承上启下的中枢之轴,是决策机构“院务委员会”中指导执行机构行政工作班子的代表。在1988年秋至1989年底,书院面临内部争执以致分裂的动荡阶段,汤先生是院务委员会和多数导师的代表,是稳定书院的决定性人物。
在90年代,汤先生是书院人、财、物、事统一的决策者、指挥者。2000年后,汤先生不再担任书院的院长、法定代表人,但据《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年(1984-2014)》,他依然是出席活动最多的书院代表者[12]。同时,他也依然是书院重大决策的灵魂人物,是“持续”推动书院的“组织”发展的精神领袖。
一个机构、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合格的领导人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务性领导人,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贡献都在其任职期间;另一类是历史性领导人,他们即使已经离任乃至离世,后人依然可以享受着他们的遗产。对于中国文化书院来说,汤一介是历史性领导人。那么,汤先生的遗产是什么?

2024年12月24日庆祝中国文化书院四十周年大会上,我以《致敬历史中的选择》为题作院长致辞,说到:
40年来,尽管有无数个放弃的理由,尽管有无数次改变的诱惑,尽管有无数种困难的压力,但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追求,中国文化书院没有变;“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宗旨,中国文化书院没有变;以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书刊编辑、专业培训为主的业务模式,中国文化书院没有变。
这三个“没有变”,就是我们继承汤先生等前辈留下的遗产并继续前行的步伐。
除了举起中国文化主体性大旗,体现出一条面向未来的传统主义思想路线,汤先生留给中国文化书院最大的遗产,一是确立了独立办院的底线原则;二是确立了开放与融合的风格;三是不以个人学术象牙塔的追求为限,始终怀有社会关切的忧思。这是汤先生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失去这三点,一切成功都不足道也!
1984年10月,因有胡耀邦批示,教育部对建立中国文化书院表示支持,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召集社科司、外事司、人事司的部门负责人开会,并邀请汤一介和北大有关领导前去参会商量。但北大的方案是在北大设一个“虚体单位”,“一切活动均需上报得到批准才能实施”,而汤先生坚持要办一个独立实体的中国文化书院挂靠在北大,最终无果而散[13]。随后中国文化书院就以挂靠北京高等学校哲学教学协会的方式独立建院。这是为书院事业确立原点的重大选择,没有这个起点,后面的历史就无从谈起。而汤先生坚持开放与融合的风格,不拘观点,不拘学派,不拘学科,甚至不拘泥于是否限于学术界,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得上他,甚至此风格一时不被理解。但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书院导师队伍群星汇聚的格局,开出了此后跨文化研究的新学术之路,开启了1993年后中国文化书院成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的转型。这两点是汤一介留给书院的事业遗产,而汤一介的忧思,则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五 汤一介的忧思与我们面向未来的命题
汤一介的忧思首先是他的一个未竟的梦想。1999年8月15日,七十二岁的汤先生给中国文化书院的全体导师和一些来往比较紧密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90年代书院平庸的生存状态的不满和自责,他说:“主要是由于我作为院长领导不力,而没有能使书院有所发展。现在将进入21世纪,如果中国文化书院再不能跟上当前发展的形势,中国文化书院将会被淘汰出局了。”于是他提出一个计划:创办一所民办综合性大学。汤先生在信后还附了一份他亲自起草的“中国文化书院筹建私立综合性大学的设想”。其中提出机构设置以“少而精”为原则,设董事会、教授会,并设党委会“监督和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的实行,党委书记作为董事会成员参加董事会”;“可考虑设五个学院:中国传统文化(国学)院;跨文化学院;法商学院;环保学院;高科技学院”;“招生人数最大不超过一千五百人(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步骤上希望“用一年时间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再用一年时间建校,于2002年招生”[14]。
2000年1月18日,汤先生写下《中国文化书院十五》〉一文,进一步提到办私立大学的意义,但他在文中也表达了对现实前景的无奈:“这也许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我多希望‘梦想成真’呀!我当了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已经十五年了,想起来真有点惭愧,对不起各位导师的信任,我的这一心情已经在8月15日的那封信中表明了。这里我把那封信和‘中国文化书院筹建私立综合性大学的设想’抄下来,那〔哪〕怕作为一分〔份〕‘档案’存盘也行!”“希望‘梦想成真’,即使不成,我也算尽力了。”此事,汤先生认真做过努力,召开各种可能性分析会议,并自己做记录。他和我说,等他筹到5,000万元就交给我来办大学,要求我到时候要全力投入;庞朴还为我分析过校长人选——“自由派”代表人物如何比“传统派”代表人物更有号召力。但因基本条件不具备,上述设想终究只能是“一份‘档案’存盘”。
近二十年后,我在参与支持西湖大学的事业时,常常会浮现汤先生给我们写这封信的情景,所以我说:历史的深邃迷人之处恰恰在于,那些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时就被平庸就地消化了,而那些当时没有成功的崇高目标却像远方的灯塔一样,召唤着后来人。那些超越了成功与失败的目标,既然以历史的名义感动了后来人,后来人也终会成就一个感动历史的故事。
而汤先生这个未竟梦想的背后是他对时代命题的深切忧思。他说:“为甚么我总是忧心忡忡,一方面我怕失去我们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也怕我们不能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不能不忧心忡忡,因为你面对现实的社会,它的问题那么多。”[15]所谓问题,在文化上都会指向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人学术传承背后的时代命题: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现代性转型;通人之学到分科立学的学术范式转型;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

今天,只要我们还没有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依然难免在传统的存续或叛逆间失重;只要我们还没有拿出全球视野里令人敬畏的学术成果——可以让西方人像我们第一次读到康德(Immanuel Kant),读到黑格尔(Georg W. F. Hegel),读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读到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一样,感到震撼的学术作品——就依然要寻思中国学术的现代范式如何确立;只要我们还没有树立现代社会公民个体的主体自觉,还不能在知识传授和社会批评外,承担对人的终极关怀和社会应然理想建设的使命,就依然要问“何谓知识分子?”
这些忧思今天依然直指人心。所以我说,汤一介的忧思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历史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历史不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可以在今天的人心中复活的过去。
历史人物所以能感召人,不仅仅因为他们高大,而且因为他们亲切,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脚上有泥土,身上有伤痕,内心有梦想、有遗憾,有对未来的忧思!
【注释】
[1] 本文引用资料除已注明外,多出自陈越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5)一书,不再另注。
[2] 参见汤一介:《汤一介集》,全十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作者简介”。
[3] 参见汤一介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派发的《汤一介教授生平》小册子,2014年9月。
[4] 杨立华、江力整理编纂,李中华审定:〈汤一介学术年表简编(2024年版)〉,载汤一介:《儒学十五论》(海口:海南出版社,2024),页298-315。
[5] 干春松:〈中国哲学的深度发掘者和当代思想的融会创新者——汤一介哲学思想及其贡献研究〉,《光明日报》,2023年1月16日,第15版。
[6] 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90)》(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第VIII部分,“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专题分析”,页128。
[7] 汤一介:〈在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国文化书院学报》(读书版),1989年9月10日。
[8] 汤一介:〈编后记〉,载《中国文化研究年鉴(1989年)》(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1990),页855。
[9]、[14] 汤一介:〈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三)〉,载《我们三代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页335;329-32。
[10] 雷原、赵建永主编:《汤一介学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1] 香港世界儒学促进会访京团宴请北京学者时黎升致辞、汤一介答谢词,1997年10月16日;汤一介就黎升食言给当时在场者的通报信,1997年10月20日,中国文化书院档案第111号。
[12] 陈越光编:《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年(1984-2014)》(北京:中国文化书院,2014)。
[13] 汤一介:〈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一)〉,载《我们三代人》,页304-305。
[15]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儒学院的对话〉,载《跨文化中国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页24。
本文首发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25年10月号(总第二一一期)之“学人往事”专栏,作者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先生。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频道特转载推荐,以飨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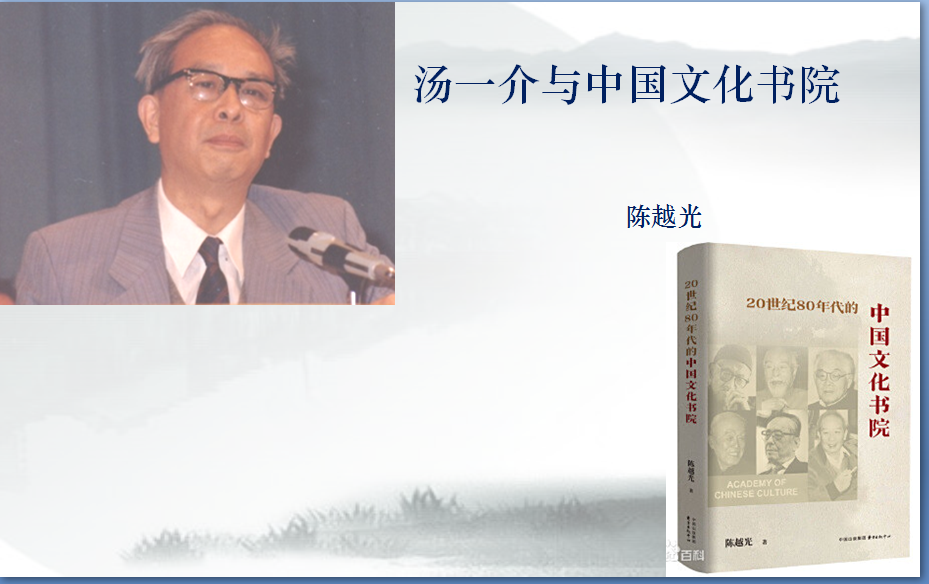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