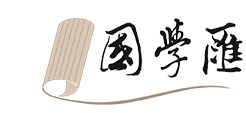
2015.10.23 第2期 作者:王立新
唐太宗命画师阎立本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图像绘于凌烟阁中,希望后来的臣子们效法,为国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甚至永垂青史。与唐太宗的做法相比,宋太祖却解除了武将的兵权,并首先确定了“任宰相当用读书人”、“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刻下石碑,传诏子孙,不管将来谁当皇帝,首先要将碑文牢记心中,不能违背,然后才可以去坐金銮殿,才有资格充任统治者,处理国家政务。如果忘记了祖训,那就是不肖子孙,连上天都不会保佑其皇位。

宋太祖赵匡胤
著名的“太祖誓碑”上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有很多学者出于求实的精神,拼命考证“太祖誓碑”是否真实存在。但是证物,也就是刻有太祖“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石碑,早已在金兵攻占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天的河南开封)的时候丢失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其实这块石碑是否能找到,或者是否真实存在,已经不关紧要了。关乎紧要的,是石碑上的誓词,宋、明两代文人都有相关的记述。石碑找不到不要紧,石碑上的话语却被记住并流传下来,丰碑早已矗立在人心之中。难道还有比人心中的丰碑传诵更加久远的石碑吗?
石碑上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文字的角度,似乎已不必说明,因为没有人看不懂这句话。但是这里所要进一步申说的,是碑文的历史性意义。
王船山先生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人无欧刀之辟。”说自从宋太祖定下“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铁令,并以诏令的方式严敕后世子孙,一直到宋代灭亡,几乎没有真正的读书人被杀的事情发生。船山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以宽大的胸怀培养读书人正气的优异的政治方略。而这种“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的做法,原本出自“贵士”的初衷,也就是出于真正尊重知识分子的优秀心态。
不得杀士大夫,就是真正的尊重知识分子。一个真正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才会产生真正的大师。这里所说的尊重,是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口号,更不是炫人耳目的说辞。
什么叫真正尊重?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尊重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信念,尊重知识分子的做法,哪怕是很怪异的做法。使知识分子真正拥有独立的尊严,独立的立场,独立的品格。而不是告诉他们听话,只会听话的不是知识分子。不听话,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只有不以“好好听话”为直接目的,而以“建立独立不倚的人格”为终极目标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与此相反的就不是教育,而只能叫做奴役。
只有在知识分子朝向理想道路前进的途程中,不必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不必要的妨害,才能培养他们坚持理想的独立个性,才能造就他们为维护正义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他们才会自觉地去承继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才会果敢地接续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生命,才会主动承担社会的责任,才会真正为朝廷效命,匡扶正义,关爱苍生,才能激发他们内心中对历史文化、对国家民族、对社会、对生民的由衷的热爱之情,才能使他们把生命中的全部能量释放并发挥出来。他们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真正向标,社会才能因为他们的倡导闻风而动,风气才能变好,人心才能向善,社会才有生气,才有正气,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国家、民族才会有真正的希望。
士大夫是读圣贤书的,辱士人即是辱圣贤,辱圣贤就是辱历史文化,就是侮辱自己的祖先,就是侮辱自己的民族!读书人一定要受到尊重,这是民族存续和国家发展的首要的前提,没有什么东西比真正尊重读书人更加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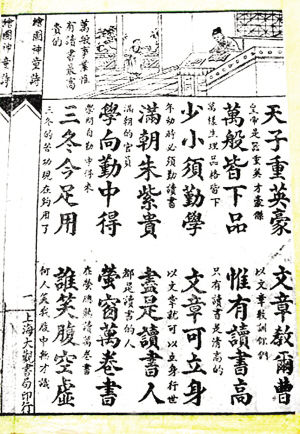
《神童诗》
而读书人一旦受到真正的重视,就会形成全社会的向学之风。“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宋代蒙学小书《神童诗》里面的开篇话语。我小时候不知道,还在批林批孔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批判《神童诗》。当时还教给小孩子们唱一首歌曲:“儒家神童诗,骗人的鬼把戏,世上无神童,实践出真知。”一共就这四句,节奏有点像日本女排的战术,短、平、快,从歌词到曲调,都给人以凶恶、暴戾的感觉,令善人走向凶狠,令胆小一点的人顿生恐惧。我到现在还会唱。其实这都是不相干的瞎扯。
实际上,《神童诗》所描画的,是宋朝时代的优良社会风尚。虽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话语,多少让实际的体力劳动者有些感觉不快,但是《神童诗》的立意,在于表彰读书,不在于藐视坚持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民众。读书可以帮助修身,读书可以帮助体会人生,读书可以扩充人的视野,增长人的识见,可以观政治的得失,了解现实的利弊,读书还可以通晓历史的兴衰,至少可以多知道很多事情,还可以帮助人了解人与人的相交之道。总之,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不是追求拿高等文凭和高级职称的风气)一旦形成,社会的风俗就会大为改观,人心就会大变,民众的心态,就会不再单纯追求利欲,而朝向善良、正义,豁达和智慧的方向敞开。

唐太宗李世民
唐宋两朝知识分子的读书心态有何不同?
宋人读书,与其他朝代不同,仅以唐朝为例来作个简单的对比。唐代在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用功利钓人的统治方针,唐太宗的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得意,自然有因科举而招揽了人才的欣喜,但同时也流露出玩弄天下士人于掌中的隐衷。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最能透露唐太宗的这种内在用心:“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在这种功利主义方略指导之下,文士们的目标主要在于猎取功名,炫耀乡里。孟郊在一首叫做《登科后》的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标准的功利性目的的自我表达。独孤及的《送虞秀才擢第归长沙》的诗句,更能表现士大夫的这种心态:“甲科文比玉,归路锦为衣。”李贺也一样,他的《南园》诗是这样写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意思里虽然有为国效命,疆场立功的想法,但是“请你到太宗的功臣榜上看看,有几个是读书人?”这样的话语,显然有明显的贬低读书的意思,是在宣传读书无用论。中国民间甚至还因此流行这样一句话语,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多么可怕的话语,竟然流行在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大地上!不读书,哪来的五千年文明?不读书,何以继承并发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与唐代知识分子相比宋代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抒发心声的呢?
我也举两个例子,王禹偁在《黄冈竹楼记》中说,自己得意于“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公务之余,读圣贤之书,用以消除世俗生活的干扰和烦恼。他在被贬谪的时候,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是如下的景致:“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慨也。”完全融入到山水之中,彷佛什么苦难都没有经受一样。王禹偁是954—1001年人,在被贬的状态下,还有这样好的心境,寄情山水,读圣贤书,涵养身心,可谓人格俊美,境界高远。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更为典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范仲淹的做法,后来被大理学家朱熹总结归纳为“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是989——1052年人。两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宋代建国都还不到一百年。就在这不到一百年的光景里,赵宋王朝已经把一个缺乏仁爱、无论正义、无视廉耻、不讲礼让的混乱不堪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人心向善,勇于担负责任,不局限于利禄的追求,而系心民族、民众和国家的存亡与祸福,企慕高远的人生境界的一个风俗美好的社会。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政绩!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历史功勋!
至于南宋,那就更不用一一列举了。湖湘学派的理论宗师五峰先生胡宏在其所著《知言》里面说:“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又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大贤之分也;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者,圣人之分也。”这是怎样的情怀?如果读书人都能像宋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中国该是怎样的社会?人间天堂也不过如此而已。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说法,而是宋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心志取向和人生目标。
宋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唐代知识分子,只图自己功名的实现。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是普遍的现象,个别例外总是有的。唐代知识分子,一旦科举得中,顺势投身权门,“苦求官禄”,数米计薪而已,国家民族的事情,多半不能真正放在心上。宋代知识分子在没出仕为官之前,就已抱定理想,心系天下苍生,心系国家安康,心系民族文化事业的传承与发扬。为什么会是这样?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唐代统治者拿功名利禄诱惑知识分子,实施的是功利主义的诱人方略;而宋代执政者则是用正大之气感化和教育知识分子,“以宽大养士人的正气”,贯彻的是价值理想主义的育人原则。
由于引导目标的不同,才导致了唐、宋知识分子的目标和行动方略的不一致。唐代知识分子重视功名,宋代知识分子重视操节;唐代知识分子追求才气的挥发,宋代知识分子强调理想的实现;唐代知识分子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宋代知识分子追求为国家民族做贡献。
宋代重视对真正的读书人,而不是一班只图拿文凭,只图谋官位,只图捞实惠的功利之徒的培养。宋代优礼士大夫,为他们提供一切发表言论、表达政见、教书育人和传承历史文化的待遇、机会和条件。这种优礼士大夫的政治方略,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献身时代、献身民族、献身国家、献身历史文化的热忱,也营造了古典的自由讲学、自由论政的民主社会风气。
所谓“不杀上书言事人”,其实是讲:人家上书发表意见,指斥你统治方略或者行政措施的不妥甚至弊病,反映社会的实际情况,你不能杀人家。你要是杀了人家,谁还会出来纠正你的错误,谁还来为你指点迷津?要知道,任何统治都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一定要有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出来讲话,这个社会才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社会的风气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给你提意见,甚至出来骂你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都是为了你好。人家是出于一份社会的良心和责任,其实谁愿意管你的乱事,尽早烂掉跟人家有什么相干?谁当皇帝,谁来主政大家不吃饭活人?之所以给你提意见,之所以骂你,那是因为爱你,这是真正的“打是亲,骂是爱”!当然,这些“上书言事”的人们,还出于对民族、民众和国家的责任,不仅局限于帮助现行统治少犯错误和改正错误。那就更需要善加保护,因为这是他们对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打压这些人,就是打压对历史、民族的责任,不仅极其不利自己的统治,而且还是对民族和历史的犯罪。犯罪不单指普通社会民众违背统治者的意愿和法规,也指向统治者对历史和民族的不负责任!而且这项罪孽更加深重,更加罄竹难书!
“不杀上书言事人”,就是保证持有不同意见甚至是不同政见的人不受打压,只有这样,社会才有“民主”可言,才会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才会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才会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和错谬。

宋初宰相赵普
“道理最大”与“任宰相当用读书人”
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初,就经常和宰相一起探讨治国安邦的道理,他问宰相赵普:“世界上究竟什么最大?”
要是其他朝代的臣子,顺口便会逢迎主子说:“皇权最大”。但是赵普却说“道理最大”!
权力,利益,亲情,关系,这些都不小,但都不是最大的,天地间只有“道理最大”。制定政策政令,要讲道理,要有道理依据。处理政务要讲道理,收税、断案要讲道理,就是处理日常事务,判断人事是非,解决民事纠纷,也要讲道理。
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项政策或者政令,甚至某件具体事情为什么非要那样做?如此做法的理据在哪里?效果预测的根据在哪里?这样的做法对现行统治、对社会、对生民、对国家、对民族,究竟有什么好处?都得问道理。没有道理或者道理不明,就不能这样做。同样,某件事情为什么不这样做?同样需要问道理。不做没道理的事情,这是为政的最基本的起点,要是一切做法都仅仅围绕着自己的统治能否维持下去,那就是不讲道理!那就是不懂道理!小事情也一样,做与不做,一定要先问问有没有道理。因为无论权力有多大,都没有道理大!不管某种措施或者某项工程获利究竟有多大,都不如遵循道理获利更大。世界上什么事情最有利?讲明道理,遵循道理最有利!

孟子见梁惠王(资料图)
梁惠王问孟子能够给她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告诉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孟子不言利,不懂利,连司马迁都这样认为。其实孟子不是不讲利,而是不讲小利讲大利。遵循仁义,就是最大的利。遵循仁义,遵守道理,就会获得上天的眷顾,《周易》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赵匡胤由衷赞同赵普的说法,君臣同心,坚守“道理最大”的原则。在赵宋皇帝和历届朝臣一代一代地坚守之下,宋朝虽承晚唐、五代之弊,社会风气贪鄙无耻之极,人心颓废无以复加,但在几十年之间,就彻底改观,人心向善,风俗醇厚,贪鄙之习渐远渐匿,廉洁奉公的风气骤然兴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奇迹般的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宋孝宗曾经对大臣们说:“太祖问赵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尝三复斯言,以为祖宗时,每事必问道理。夫焉得不治?”凡事必问道理,先问道理,国家怎么会治理不好?
孝宗的话语,表明到了南宋的时代,赵匡胤的子孙们还在坚守“道理最大”的原则,按照“道理最大”的原则治理国家。凡事首先要问有没有道理,合不合道理,这就是宋代的君臣。这样的政治国家,是很难走上绝对的独裁和专制的道路上去的,也不会被天下人所遗弃,成为实际上的孤家寡人。
有了“道理最大”,并将“道理最大”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充满民主的气息,真心诚意的参政、议政,就会成为社会精英们习惯性的做法,社会生活也同样会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获得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有关“道理最大”的这段对话,被后世赞誉为明王尧、舜和贤臣契、稷之间的对话。“道理最大”,是宋代皇帝的传家之法,这个家法定下了宋代政治的基本格调。这项原则,一直被宋朝的各代皇帝和臣僚们带到了血如夕阳的宋朝之末。
“道理最大”“任宰相当用读书人”和“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使宋朝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人心拥戴。在这方面,远远超过汉代和唐代,元明清更不足以与宋朝相比。元代的许有壬说:“宋养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轶唐、汉而远过之。”说宋代在优礼士大夫,从而赢得士人真心拥戴,盛况空前,远远超过汉唐,绝非汉唐两朝所可比拟。
宋朝用“道理最大”,挽救汉、唐以来的绝对专制带来的严重社会弊端,使为官一事,不再专为拥有权力而设,不再成为谋取私利的条件和手段,使所有的各种权利的拥有者们知道:“权利不如道理大”。同时,“任宰相当用读书人”的国策,极大地鼓荡了天下人读书的热情,朝野上下风气大变。赵宋王朝就以这样的治国原则和治国方略,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质彬彬”的生民社会。而“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则有效地保护了不同政见者的合法权利,使统治集团能够不断的听到与自己的统治方略不同的声音,从而不断地修正统治的错误,不断地使自己的统治方针朝向符合社会实际的方向改进。生民的苦楚,得到了必要的伸说和倾泄,没有淤积成巨大的社会隐患。有宋一代,并没有出现像汉、唐、明、清等重大的内部祸乱,与这项国策有直接、重大的关系。
“道理最大”、“任宰相当用读书人”、“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以此三点为核心内容,构造起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大厦。君主的诚心,赢得了士人的忠心,赢得了民众的欢心。以至于宋朝在那样的内忧外患之下,面对人类历史上任何王朝都不曾遭遇过的辽、夏、金、元的强敌(就元朝之强而论,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强悍的外敌,其不可想象的野蛮和凶顽,简直就是外星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遇见过。凯撒、拿破仑和希特勒等,没有遇见成吉思汗,算是他们运气好),依然能够坚持那样久,而且在国家实在无力支撑之时,官僚、士大夫们纷纷挺身而出,慷慨赴死,仿佛人类的历史已经结束,甘愿与大宋王朝一同化为齑粉。这种悲壮与绚丽的风景,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断然没有第二次出现过!

顾炎武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宋代知识分子满含忠义之气,以名节为高,以廉耻相尚,“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就是说宋代“讲道理”和真正尊重知识分子的政治,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忠心,激发了他们为大宋王朝英勇效命的由衷热忱。从北宋靖康年间金兵毁掉北宋政权,直至南宋最后毁灭于元兵之手,160余年之间,宋代为国死难的忠烈之士,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前后呼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牺牲的志士,虽然舍弃了生命,但他们的精神,却像一道互相链接而成的绚丽的彩虹,永远的高挂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上空,光彩夺目,光耀千秋!
写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清代学者赵翼,在其所著的历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里也说:宋代对待士大夫的宽厚,使得他们完全不必为生计而忧烦,从而能把全部精力用在为国家的兴亡和民族文化的兴衰的考虑上。“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赴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宋代对知识分子的优礼,赢得了超常的回报,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知恩图报,平居,则严于律己,教育子侄;为官,则清正廉洁,为民请命;被贬,则思念君王,心忧天下。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奋身投入拯救,拯救无望,则以身殉国,绝不苟且存活世间。宋代为国家牺牲的烈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相提并论,为宋代而牺牲的英烈,比全部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中,为国家和君王死难的全部总和还要多出不知多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宋朝统治者不以手中握有的绝对统治权力欺凌人,不以自己掌控的强大武力的威慑恐吓人,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实施对文化思想的钳制去恶心人。
在皇帝带头倡导,朝廷大臣以身作则,天下文人、士大夫踊跃投身之下,宋代文化昌明,人心醇厚,社会风气正大刚健。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明清时期,有人指责宋代的士大夫和理学家们,说他们“平居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说他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抱个膀儿在那里谈论心性问题,等到国家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没有好的拯救方案,只是一死了事。这种所谓的批评,除了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客观全面的了解之外,还表现为:小视壮烈牺牲的豪迈,蔑视为国捐躯的勇烈,无视为正义而慷慨赴死的感天动地!
“道理最大”,还奠定了宋朝文化繁荣,理学昌明的重要政治统治方略基础。因为只有“道理”最大,“道”才最大,“理”才最大,“道学”和“理学”才被看重,道学宗主和理学开山祖师才会有地位、有影响力。周敦颐能够“被做大”,正是宋代统治者崇高的政治理想的需要使然,也是宋代知识分子“参赞”圣德的积极努力的最大成效之一!同时,又是在讲道理的宋代社会的大趋势和大风俗的背景的烘托与陪衬下,必然产生的客观结果。

《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皇城
只因知道“道理最大”,宋代才是真正的大宋王朝。其余如唐朝、汉朝和明朝、清朝等,都没有资格被称为“大唐”、“大明”、“大汉”和“大清”,因为这些王朝都不知道天底下究竟什么最大,他们或者以为利益最大,或者以为权力最大,就是不知道“道理最大”。换句话说,就是他们都不懂道理,更不懂“道理最大”。连天底下什么最大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叫做“大汉”、“大唐”、“大明”、“大清”呢?如果一定要这样称呼,意义也只能限于武力强大、利益最大、疆域辽阔和自以为是等的虚妄称谓。其实也只是臃肿肥大而已,用民间话语说,就是“虚胖”,需要“减肥”才行。只有宋朝,才可以叫做“大宋”。因为“大宋”的“大”,不是疆域、权利、武力和财力大的意思,而是“伟大”的大。只有知道“道理最大”的王朝,才是真正伟大的王朝。
(本文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先生授权凤凰国学独家发布,节选自其专著《理学开山周敦颐》,岳麓书社出版,略有删节。转载请注明出处。)

王立新: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驻心宋明儒学的研究。

凤凰国学 官方微信
传承东方智慧
涵养中华气象